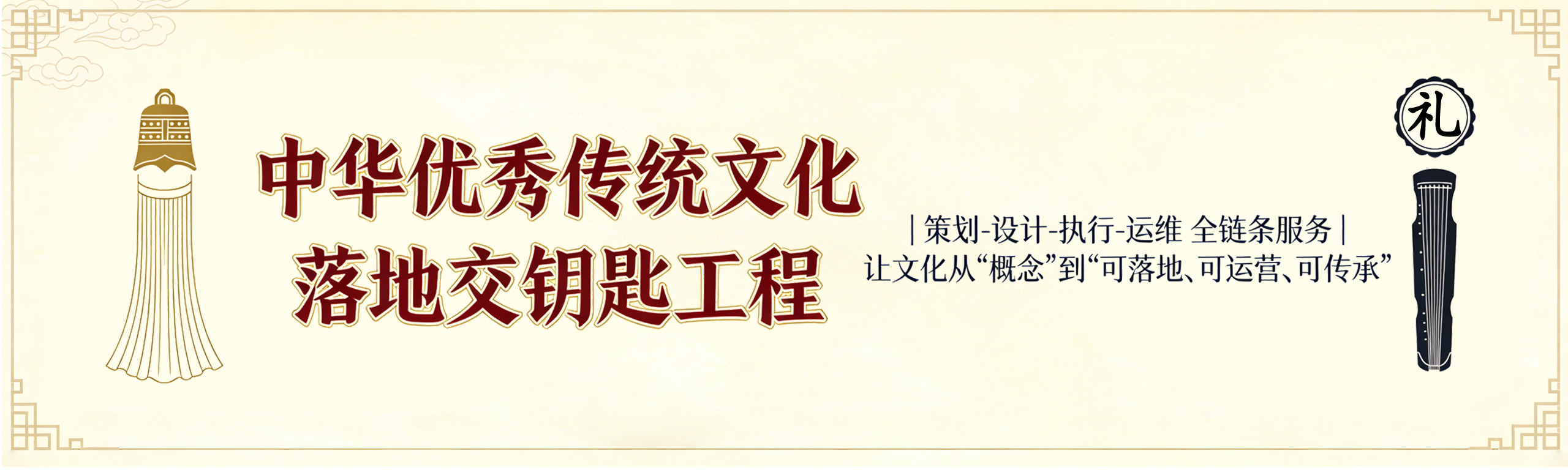来源:《孔子文化》第20期
作者:陈岳
(续上文)
三、由“一”始:孔子思想逻辑起点
孔子讲“吾道一以贯之”,是用“一”来概述整个自己所接触和阐发的文化,是一种抽象的表达方式,实有重要的意义。中国数字并不是简单的数理含义,能用“一”来贯通,应与其代表含义有关联。《孔子家语·礼运》篇中讲“夫礼必本于太一,分而为天地,转而为阴阳,变而为四时,列而为鬼神”,这里的“太一”的概念,是否与孔子所讲的“一以贯之”中的“一”是一致的?
《老子》中说:“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盈,王候得一以为天下正”,这里的得一指获得本源,本源是什么?是气,是水,还是道?这些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一”这个本源代表了整体与所有,存在着的与不存在着的,这之中它们纵向连续,横向联系,“得一则必得二”、“得二则必得三”,“一”本就可以生二、生三,在二、三中有药首先把握这个“”,可以说把本源简化为“一”的时候,它所代表的就是这个思维运动,而不是固有物。黄克剑曾说,“孔、老之道;通而不同,注定了‘教’或‘教化’的通而不通,而两种‘道’和‘教’的通而不通,则又注定了两种‘无为而治’的‘为政’观念的通而不同”。所以孔、老所通的地方是“合于那个时代的致思逻辑的”。

从史书记载中孔子与老子的对话来看,老子讲孔子所学是“其人与骨皆已朽”,不仅有所来源,而且时代久远。而老子所谈也是“闻之”的内容,这里有可能是老子的谦辞,但结合《左传》-书多谈“古之制”与“所见、所闻、所传闻”的说法,老子的学说未必不是有所承接。对于儒、道两家的关系问题,学者们多有不同的见解。但要指出的是,孔、老关系并不等于儒、道关系。当代学者分析儒、道两家异同时,往往会混淆了这两个概念。孔、老治学之初,非为成一家之言。从宏观上看,两者都是对三代文化的承接、研究和发挥;从微观上看,则是对当时流行文化的系统学习和对当时存在问题的讨论。换言之,先秦诸子拥有共同的哲学本体。
从这样的角度来看,把“一以贯之”中的“一”看做是一个本根性的存在是有-定道理的,而在历史上何晏、王弼、朱嘉等人在解释时正有如此含义。
夫子讲自己的道是贯通的,是在讲其思想有着内在的逻辑。逻辑的前提是“一”的思维方式,逻辑的过程则是从“一”作为本根性的含义开始,所以夫子用“一”来贯通“道”。夫子整句话的含义与老子道生论的意思相近,他们都持有这种宇宙生成论(本根论)。子很少论及形而上的“道”生万物,但却常常论及人与“道”、人与天地的关系。相对老子关注本体论来说,孔子更加关注其方法论的运用,故而孔子追求“中”。
老子讲“侯王得一以为正”,“以正治国,以奇用兵”。孔子言“夫礼本于大一”,“人道政为大”、“夫政者,正也”。孔、老都讨论过这些概念,而且这些概念的相似之处,足以证明孔、老在认识到“一”之后,只是在“一”生二、生三、生万物的变化之间选择了不同的道路
四、孔子学说的内在逻辑过程
借助老子的思想,我们可以梳理出在孔子学说的内在过程。简单说,在“一生二”的中,需要分定,分定就要有度,这个度就是“中”,至于“二生三”的过程中要“复相辅”,这个过程所求的正是“和”,所以在《中庸》里讲“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如此思路之下,问题便变成了“如何中?如何和?与“哪些中?哪些和?”的问题。基于这个问题,夫子提出了作为人的核心价值理念,包括内在的精神力量、社会伦理道德以及外化的“礼”,并通过“诚”的方式与天地融合在一起,终究用行动通往“大同”世界。
人在中国古代的观念当中本于天地所生。《礼记.礼运》中便讲“故人者,其天地之德,阴阳之交,鬼神之会,五行之秀气也”。老子论人,求“守弱”、“居为不争”、“寡欲”,实际是从天直接到人,省去中间论述的环节。而孔子则是更深人、更细致地揭示人内在与外在的联系,也就是在文献当中常见的“情、性、欲、心”等与“命、天、气”等的关系。郭店简《性自命出》篇讲“性相近,习相远也”,“道四术,唯人道可道也”,就是因为人性具有动态,具有感物而动的特点,才会有所差别,便会违背“一”生万物的主旨。这个主旨即是“天地位”、“万物育”。因此人才要“习”,术才要“道”。《中庸》中提到:“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这样的言论正是孔子思想中本一的最好体现。
“本一”就要“用一”,就是将“一”变化的方法用在人事当中,“用一”就是“用中”。“用中”是将喜怒哀乐发而中节,就是中节人欲人情,做到恰当、得位,做到符合“一”,也就是《乐记》中讲的“将以教民平好恶而反人道之正也”。“用中”就是要使人道得正。
《说文解字》中徐错注“正”为:“守一以止也”。人道之正就是要合乎“”,老子亦言“侯王得一而以为天下正”。“一”与“人道之正”的关系显露无疑。
孔子言“吾道一以贯之”,这个道未必只有“人道”,但在涉及到人道的时候,孔子言求其“正”。《孔子家语·大昏解》中哀公问政时,孔子说:“人道,政为大。”《大学》讲:“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中庸》讲:“天下之达道五,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天下之达德三,曰:智,仁,勇。”“明德”、“新民”、“至善”、“五达道”“三达德”都是“人道之正”,《孔子家语·王言解》中说:“夫道者,所以明德也;德者,所以尊道也。是以非德道不尊,非道德不明。“道就是德,体用两分而已。“子日:‘中庸其至矣乎,民鲜能久矣’”(《中庸》),中庸是最大的德,是本一而用一,所以孔子讲“一”。曾子言“忠恕”,“中心为忠”,就是返回到性当中。“行己为恕”,考虑他人,能尽己之性,能尽他人之性,能尽物之性,所以“忠恕违道不远”,正是这样的含义。
先民体会到“一”的变化,将“中”作为传承下来的理念,影响了人们的思维方式、行为手段等等。从某种程度上说,“礼”正是在对“中”的继承和理解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礼所在,正是用中的表现,“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矣”,只要做好礼,就可以“王中心无为也,以守至正”。这里的“礼”与现代意义上的礼含义是不同的,它不仅仅是行为规范、生活仪式,它还是一种制度。
作为行为规范和人生礼仪,礼的制定与人本身是密不可分的。礼是要“治人七情,修十义”,就是用中于人。在“必知其情,辟于其意,明于其利,达于其患”的前提下,用合乎“中道”的“礼”规整人的行为,比如如何对待长辈、朋友,如何待人接物等等;正确的看待人生中的种种重要阶段,比如成人、婚姻等等。
不仅仅是礼,孔子学术的内容、目标都是归于“一”的,《礼记.乐记》中孔子所教授的六经,所谈论的礼乐、道德、政刑,实际都是要归于“”。这个“一”就是“治道”,就是“大道之行”的“大同”社会。而走向大同社会的途径就是礼乐,就是用中于人事,而达到“人道之正”。
礼,“欲一以穷之”;乐,“审一以定中”。礼乐相和之至,是孔子心中的大同社会。《公羊传》中讲“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刘尚慈先生在解释“大一统”时写道:“始于一, 归于一的王道政治”。这种王道政治正是西周时期形成的礼乐文明,它是一种和谐的境界。这种和谐是由内而外的,是人与外在的统一,是建构在人的心理情感之上的。不仅仅是与社会关系,还与自然界达到“天人合一”的状态。这种和谐,追求的是在个体的完善下走向社会的大同。这样的统一,不仅仅是人道,更是整体下的“归一”。(本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