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孔德成
禮在儒家思想中,佔有極重要的地位,自孔子時就是如此。內而個人之休養,外而使社會人群,各得其安定之分,這都是禮之份內的事。所以儒家的禮,包括著律己處人的規範、社會的秩序、政治的制度。現在我們分別來談談。
一、儒者對於禮之普通原理理論及其功用
孔子是一個重視禮的人,不過沒有提出正式的普通理論來。到了最注重禮的荀子,才提出禮的普通的理論根據來。《荀子‧禮論篇》 論禮之起源說:
禮起於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則不能無求;求而無度量分界,則不能無爭;爭則亂,亂則窮。先王惡其亂,故制禮義以分之,以養人之欲,紛人之求,使欲必不窮乎物,物必不屈於欲,兩者相持而長,是禮之所起也。
《荀子》這段話,是說明禮的起源的原因,根據人的心理,用「定分」來節制人的欲望的,以免人與人之衝突,人與物之屈窮。這個理論在《禮記‧禮運篇》裡也有說過:
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貧苦,人之大惡存焉。故欲惡者,心之大端也。人藏其心,不可測度也。美惡皆在其心,不見其色也。欲一一窮之,全禮何以哉?
這是說明人的心理的好惡,美惡,是不可測度的。故須用件事物來作標準的衡量,才可以窮究人心之莫測高深的演變,這個標準,就是禮。也就是說,樹起這個禮的規範,才可以將人心歸納到一個範疇裡來。至於像〈禮運〉、〈樂記〉等篇,更將禮的起源,根據的理論,本於天地四時。在抽象的觀念上,有他玄妙的道理,不過就與原始的禮的理論來說,是應當有相當的差別了。
我們再說禮的用途,除如上引《荀子》所說防人與人之衝突外,是進一步的調和一己自身諸情欲的衝突。以一方面「節」人知情,「文」人知情,而使他得到「時」、「中」。《論語‧學而篇》上有若說:
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合而合,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

《孟子》也說到節文二者,〈離婁上〉:
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
有若和孟子,都是主張禮在人情方面有其節、文功用的。什麼叫作節?就是一件事情,作的不要太過,也不要不及,得其中道,就叫作節。《禮記‧仲尼燕居篇》記載後人轉載孔子的話說:
仲尼燕居,子張、子貢、言游侍。……子曰:「師爾過,而商也不及。子產猶眾人之母也,能食之、不能教也。」子貢越席而對曰:「敢問將何以為此中者也?」子曰:「禮乎禮!夫禮者,所以制中也。」
這裡所說禮以制中,就是用禮來作人情之節制,不使其過,不使其不及。《禮記‧檀弓篇》裡也說:
曾子謂子思曰:「伋,吾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於口者七日。」子思曰:「先王之制禮也,過之者俯而就之;不至焉者,企而及之。故君子之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於口者三日,杖而後能起。」
又一段說:
子夏既除喪而見,予之秦,和之而不和,彈之而不成聲,作而曰:「哀未忘也,先王制禮,而弗敢過也。」子張既除喪而見,予之秦,和之而和,彈之而成聲,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至焉。」
這一節更可以說明了「過之者,俯而就之」「不至焉者,企而及之」,這一種心情的描寫,也可以看出孔門弟子們之禮為調和一己自身之衝突的工具。「文」就是禮的外在的一種文飾,禮本來是外在的儀節,沒有「文」,怎麼能表達出來?所以《論語‧雍也》,孔子說:
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史掌文書,多聞習事,誠或不足。)文質彬彬,然後君子。
如祭之器、服、喪之服、期,這都是文。沒有這些文,是沒有法子表達內心的情感來的。《荀子‧天論篇》也說:
君子以為文,小人以為神。
至於時呢?是說吾人既知禮的原理,則其具體的禮,是可以因時而變動,不必墨守成法,只要不違背了禮的原則就可以的。《禮記‧禮運篇》上說:
故聖王脩義之柄,禮之序,以治人情。故人情者,聖王之田也。脩禮以耕之,陳義以種之,講學以耨之,本仁以聚之,播樂以安之。故禮也者。義之實也,協諸義而協,則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柄、情乃受法家之影響者)
這是挪人情比作田地,禮比作耕地。田都是土的,耕就得要看田的情形,定其耕耨的辦法。這個辦法,就是義。義者,宜也。那麼,什麼叫作合宜呢?那是因時間空間而定的,所以古禮所無,只要合乎義,就可以來一番創作。儒者並引述古代的史實,以作這個理論的依據,《禮記‧禮器篇》上說:
禮,時為大……。……堯授舜舜授禹,湯放桀武王伐紂,時也。
〈樂記篇〉上也說:
五帝殊時,不相沼樂;三王異世,不相襲禮。
又如上引〈檀弓〉上記載孔子的話,這都是說明禮之時義關係重大。
二、禮之關於律己處人之道,及其在孔門中為教育工具之一
《論語‧泰伯篇》孔子說一個人的學養是:
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
這是說一個人,能率然自立,而不為事物所搖奪,必須有禮的修養和工夫。《論語‧衛靈公篇》,孔子又說:
君子義以為質,禮以行之。
這是說君子用義以為本質,用禮來推動他覺得合乎義的那些事情,〈泰伯篇〉孔子又說:
恭而無禮則勞,慎而無禮則葸,勇而無禮則亂,直而無禮則絞。
這是說恭公、慎、勇、直這四種行為,雖都是美德,可是若果不用禮來作他的規範,以為「節」,以為「文」;則必有勞、葸(畏懼貌,不敢進也)、亂、絞(急切也)的毛病,也就失去了這四種他原有的美德了。
由上我們知道,禮本來就有注意社會的規範,對於個人制裁的趨勢;儒家中《荀子》最注重禮,更擴大了禮的範圍,凡先王之遺訓,後王之明教,人事之條理,事節之平正,皆謂之禮(見〈修身〉,〈正名〉,〈禮論〉諸篇,《禮記》諸篇亦是如此。)並且把法也加入禮中了。〈勸學〉:「禮者、法之大分,類之綱紀也。」〈修身〉:「故學也者,學法也。」又云:「故非禮是無法也。」這種介說禮字,在儒家全為新說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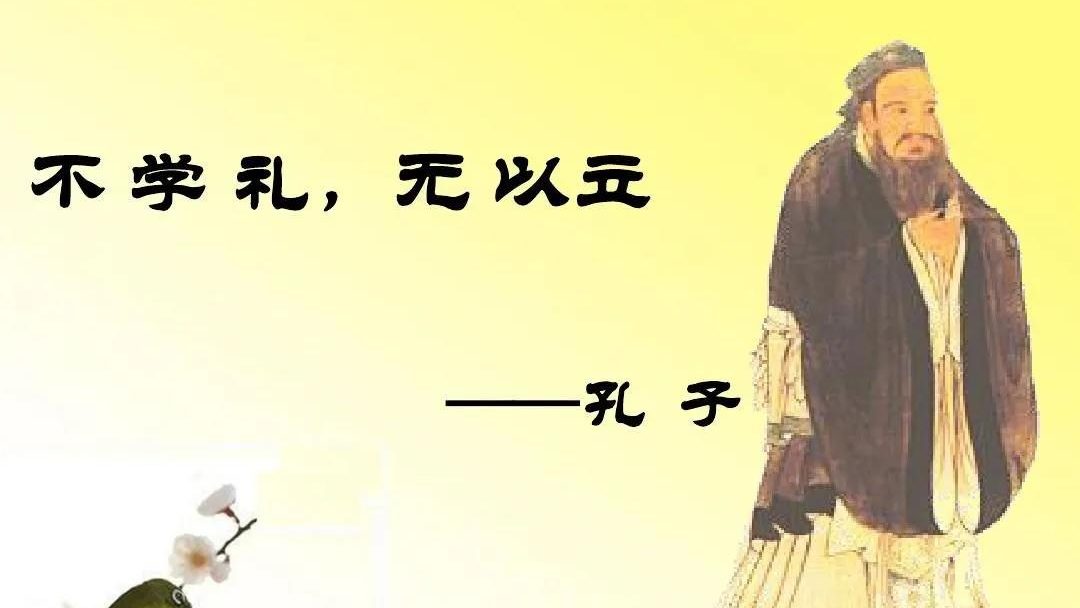
因為禮與一個人的修養、品德,既如上述,那自然就不能不成為以教育為重的孔門的教育工具了。所以孔子教導孔伯魚有兩件事,一件就是:
曰:「學禮乎?」曰:「未也。」曰:「不學禮,無以立。」鯉退而學禮。(〈季氏篇〉)
立,就是學作人處世之道,可以站在社會上,人群裡,立定腳跟,否則是站不住的。因為品節詳明,德性才可以堅定。孔子教顏淵,也是說到禮: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請問其目。」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論語‧顏淵》)
這是孔子教誨他的最得意弟子顏淵,教他注意的事項,和要作的工夫。這是什麼呢?就是「克己復禮」。克己就是一個人能克制自己,不為外物所引誘,而不可任行為所欲為。復禮,就是人群原來應當率循而行的一切規範。禮失去了,趕快把他再恢復起來。所以能夠達到「克己復禮」這步境地,就得要有「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這四種的工夫。視、聽、言、動都合乎禮,也就算是仁道了。
《論語‧鄉黨篇》裡,可以看出孔子一舉一動,都是以禮自範的。荀子教學也是以禮為重,〈勸學篇〉說:
其學惡乎始?惡乎終?曰:「其學則始乎誦經,終乎讀禮。」
由上我們知道,孔子、荀子皆是注重以禮為教的。孟子因為是性善主義,內本論者(「萬物皆備於我矣」)。所以在這一個思想的邏輯的系統之下,是不太注重外在的禮教的。所以孟子也就不太說禮。在儒家周禮上,以六藝教人,仍以禮列為第一。這可以說是,仍襲孔門之舊規的。
三、禮之關於政治及制度者
儒家在這一方面,是主張大體從周禮的。如〈八佾篇〉孔子說:
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文盛貌)乎文哉!吾從周。」
不過有時也是兼采四代。如〈衛靈公篇〉:
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舞韶。
在這幾句話裡,說明了孔子對先代的政治制度的取舍。所以後來儒者之有主張法先王的,也有主張法後王的不同的說法了。不過孔子雖是或從夏、或從殷、或從周,但是對於當時──春秋的時候,所改變的一套,多半是不贊同的,不過如果他認為合宜的,也可以遵從。否則,則不從之,仍然是遵守舊典的。如《論語‧子罕篇》上孔子說:
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眾;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雖違眾,吾從下。
這也可以看出孔子的主張是以「義」為準。至於個別的政治制度,如覲、聘之禮(《儀禮》有專篇)官制之設(《周禮》),此處不能詳舉矣。
四、禮與社會方面者
我們知道儒家是注重倫理道德的,而且是固有的家族制度的維護者。道德本來只是種抽象的觀念,如果想把他見諸實施,必須有一種組織在社會上,作為依據,這才能把他樹立起來。儒家的倫理道德之施行社會,為社會樹立一秩序者,其組織即基於家族社會中的「宗法」是也。
什麼叫作宗法呢?宗法就是家族社會中,子孫繼承的一個法則。父死子繼,傳長傳嫡的一個繼承法。這個法,本是中國舊有的,並不是創自儒家。不過儒家承襲了他,更加以細密的組織罷了。如《詩經‧大雅‧板》:「大宗維翰,宗子維城。」又如《左傳》僖公五年,晉士蒍諫晉獻公「君其修德,而固宗子。」在金文上也有「大宗」「宗婦」之稱。可見「宗法」其制亦竟很久了。不過在《詩經》上、《左傳》上、金文上都未有對於宗法制度的一個詳細的說明。現在最詳細的是在儒家經典的小戴《禮記》裡邊有兩段記載,這是我們今天能看到的比較最詳盡的關於宗法制度的史料。
一、〈喪服小記〉:
別子為祖,繼別為宗,繼禰者為小宗;有五世而遷之宗,其繼高祖者也。
二、〈大傳〉:
別子為祖,繼別為宗,繼禰者為小宗。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百世不遷者,別子之後也。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尊祖故敬宗,敬宗,尊祖之義也。有小宗而無大宗者,有大宗而無小宗者,有無宗亦莫之宗者,公子是也。公子之公,為其士大夫之庶者,宗其士大夫之適者,公子之宗道也。(注意:「別子」鄭玄以為諸侯之別子)(諸侯無氏)。
這種詳細的分別,是否合乎傳統的宗法,是否合乎孔子所主張的傳嫡(〈檀弓〉)之制,當然不敢說的。不過儒家的宗法之所以成為他的社會組織,這兩段確是他精義之所在。再就喪服的制度,用斬、齊、大功、小功、緦,這五服,把上、下、旁,所有的屬親,都組織成一個親屬網。《儀禮‧喪服篇》記載的非常詳細,《禮記》也多有專論。
五、儒家關於喪禮之主張及賦予之理論
喪禮,當然是儒家最注意的。上面一節已經說過,這裡只說說他的觀念和理論。《論語‧陽貨篇》記孔子答宰我說:
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予也,亦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
《荀子‧禮論篇》上也說:
凡生天地之間者,有血氣之屬心有知;有知之屬莫不知愛其類。今夫大鳥獸,則失喪其群匹,越月踰時焉,則必反巡過其鄉,翔迴焉,鳴號焉、蹢躅焉,然後乃能去之。小者至於燕雀,猶有啁噍之頃焉,然後乃能去之。故有血氣之屬,莫知於人。故人於親也,至死無窮。將由夫患邪淫之人與,則彼朝死而夕忘之。然而從之,則是曾禽獸之不若也。夫焉能相與群居而無亂乎?將由夫修飾之君子與?則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若駟之過隙。然而遂之,則是無窮也。故先王為之立中制節,壹使足以成文理,則釋之矣。
儒者對於死者,既然持如此的觀念,那麼應當取一個什麼態度呢?《禮記‧檀弓》引孔子的話說:
之死而致死之,不仁而不可為也;之死而致生之,不知而不可為也。是故竹不成用,瓦不成味,木不成斵,琴瑟張而不平,竽笙備而不和,有鐘磬而無簨虡。其曰明器,神明之也。
荀子說:
禮者,謹於治生死者也。生,人之始也;死,人之終也。終始俱善,人道畢矣。故君子敬始而慎終,終始如一,是君子之道,禮義之文也。夫厚其生而薄其死,是敬其有知而慢其無知也。……故死之為道也,一而不可得再復也。臣之所以致重其君,子之所以致重其親,於是盡矣。……喪禮者,以生者飾死者也,大象其生以送其死也,故事死如生,事亡如存,(據郝懿行校)始終一也。(〈禮論篇〉)
這也是基於情感、道德,功能以立論者也。也是沒有什麼迷信的意味的。

六、儒家關於祭祀之所賦予之理論
因為祭、喪,在儒家中,是很重要的,所以特別提出一說。
祭,是祭祀祖先和百神;喪,是父母諸親屬,死後的一種儀節和制度。儒家在這方面,也是承襲「固有文明」,不過都賦予他們新的理論。先說孔子的態度:《論語‧八佾篇》孔子說: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
又說:
吾不與祭,如不祭。
由上邊兩句話,可以知道孔子對於鬼神是處於半信半疑的態度的,所以祭時則覺神在,不祭時,則無神矣。因此孔子答子路鬼神生死之間說:
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先進篇〉)
又說:
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雍也篇〉)
孔子以人們還不懂得事人的道理,何能知道事奉鬼呢?人對於如何生存於宇宙之間,還不明白;那裡還曉得死了以後,又是怎麼著呢?孔子雖不以鬼神為真有,然既不說其果無,所以仍然以「敬」的態度來事鬼神。《論語‧子張篇》:
子曰:「祭思敬。」
不過,如果敬鬼神,而就真的限於鬼神迷信之中,那就叫不知(智)。孔子一方面以為不智,一方面仍存敬心,所以我們說孔子對鬼神是半信半疑的。孔子既是如此,所以他的弟子曾參對於祭禮說:
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學而篇〉)
《荀子》也說:
雲而雨,何也?猶不雲而雨也。日月食而救之,天旱而雲,卜筮然後決大事,非以為求得也,以文之也。故君子以為文,而百姓以為神。以為文則吉,以為神則凶也。(〈天論篇〉)
《禮記‧檀弓》上說:
惟祭祀之禮,主人自盡焉耳,豈知神之所饗?
舉出這幾條,最足以代表儒家對於鬼神的態度。曾子所注意者,在「民德歸厚」之效果;荀子注意其行禮時之文;〈檀弓〉上所注意的,在感情之自盡,都沒有迷信的意味。
七、儒家之禮的基本精神
我們在上邊,已經把禮所包括的各方面,大略的說了一說。我想在此處,提出儒家對於禮的基本觀念和態度。根據論語上,把孔子的基本觀念和態度,歸納出幾點來:第一是仁。《論語‧八佾篇》:
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注意:仁為人之全德,包括甚廣,此不能詳論。)
這是說人如果沒有仁德,則禮不為其用也。第二是讓。《論語‧里仁篇》:
子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不能以禮讓為國,如禮何?」
這是說禮的基本精神在於讓。
再進一步說,孔子以為道德應在禮之先,所以子夏以「禮後」(〈八佾〉)為疑,而得到孔子的讚許。
孔子雖不反對──並且親自實行那繁文縟節的禮(如〈鄉黨〉所記),可是,他以為如果二者不能兼顧的時候,與其是祇注意末節,不如只注意其基本精神。所以他說:
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鍾鼓云乎哉!(《論語‧陽貨》)
林放問禮之本,子曰:「大哉問!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治也)也,寧戚。」(〈八佾〉)
祭思敬,喪思哀,其可已矣。(〈子張〉)
《禮記‧檀弓上篇》子路引孔子的話說:
喪禮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祭禮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
這都是說明了孔子能注意「禮之本」。
總之,儒在古代,本為典章學術的寄託之專家,其初即為注意倫理道德,及建立社會之秩序者。至晉以後,法典與《禮經》並稱。《周官》之說,又悉入法典。故二千年來,儒者之學說,影響於華夏,最深最鉅者,實在制度法律公私生活之方面。這些都是儒家所謂之禮(觀《荀子》、《禮記》可知)。故禮實為儒家思想之重心。若果研究儒家的思想,能在禮的方面,多所注意,則其思得過半矣。
《中央研究院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1981年10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