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一带一路》国学文化翠峰山论坛文集
作者:任遂虎
(接上文)
好生之德,费在尊重生命成长的规律,以便生物尽其天性,享其天年,成其天乐,从而形成自然生态的良性循环。孟子讲的“不忍之心”,王守仁讲的“仁之与鸟曾而为一体”,就是要求将人性、善性向生物界伸展,不强行干预生物的生长过程。人为地强扭正如揠苗助长,的做法一样,终究要破坏生命体的发育成长。《世说》中记载了这样一事:有个姓支的的人别人送他两只鹤。他怕鹤飞,就将鹤翅上的翎羽剪去。鹤欲飞不能,左右转头看翅后,垂下头,如有懊丧之意。一位姓林的名流说:“既有凌霄之姿,何肯为人作耳目近玩!”于是,他将鹤养到羽毛长出后,让它自由飞去。这个故事,体现了古人好生、放生的情怀。没有亲和万物、善待生物的灵性境界,是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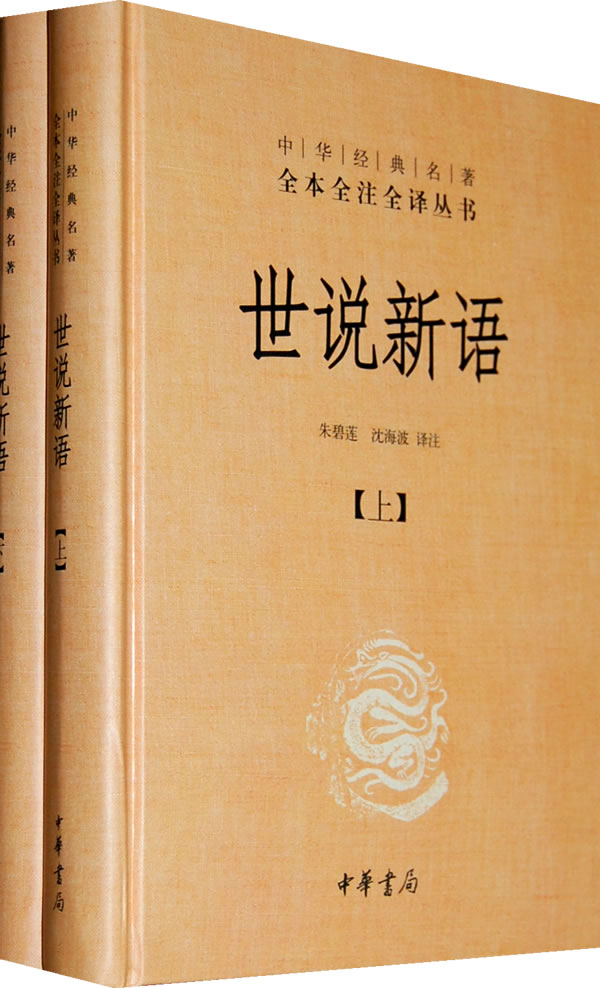
护生、放生,出于对大小生命的真诚关怀,甚至体现出悲天悯人的宗教内涵。《易经》中体证生的情怀,已具有隐秘的宗教色彩。道家法天贵生的思想取向,包容了宗教般的虔诚在古圣先贤看来,尊重和呵护生命,不仅仅是赠恩施惠,而是贯彻字宙大化流行的法则,引务天地精神的神圣与尊严。佛教传入中国后,悲天悯人的宗教情怀与本土文化中法天责生的思想融为一体,成为尊重自然、尊重生命的内在的精神动力源泉。文人学士的创作,从审美角唐任现了道教的节欲行善和佛教的断欲解脱。节欲行善和断欲解脱的共同指向,就是乐善而恶杀惜物而爱生。陆甫皇《居士》一诗写道:万峰回绕一峰深,到此常修苦行心。自扫雪中归鹿迹,天明恐有猎人寻。”诗中的修炼者怕猎人来打鹿,便将留在雪上的鹿脚印迹扫去。不难看出,灵性修持结出了维护生态平衡的“正果”。至于职业的宗教界人氏,则以因果报应的说教来说明杀生会酿成恶果。如仰弥居士有这样一首诗:
天生动物与人同,一体涵濡覆载中。
底事忍心行杀害,酿成灾劫恼天公。
诗的意思是说,暴珍天物,残害生命,会惹恼上天,那么恶报就在所难免了。因果报应论验响了一个道理:不计后果的棉取,最终是人与自然俱毁。人类肆无思惮地破坏自然,必然引自然的报复。想天例人,是普良的体现,是情感的结晶。善待生灵,在定的意义上是善自身、这种对“无心的敬奉,对“天道的畏惧,客观上有利于维护自然生命的繁行生息。
不难看出,佛教尊重生命的情怀是传统生态意识的灵魂资源。
五、国学生态观对当代人类的昭示
法天地而贵生物思想,体现了理性与情感的统一,功利与审美的统一,目的与规律的统:现世与超越的统一,时间与空间的统一,人与自然的统一。这理论致思的价值取向对三类社会具有冷峻而绵长的昭示和启发作用。
《中庸》中说:“ 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上律天时,下袭水土。譬如天地之无不持载,小德川流,无不覆帱。譬如四时之错行,如日月之代明。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俘。因其大德数化。此天地所以为大也。”朱熹注释道:“律天时者,法自然之运。袭水土者,因其一定之理。”律天时,就是尊重自然规律。自然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人不能蔑视和对抗自然规律。人作为自然的产物,只能认识和掌握规律,而不能创造和消灭规律。孟子认为,人只有既“乐天”又“畏天”,做“天民”而行“天职”,才能受“天禄”而享“天福”,得到自然的回报和恩赐。朱熹把“乐天”解释为“自然合理”,把“畏天”解释为“不敢违理”。按儒家的原意,人的天职就是维护自然的生道。“律天时”的古训昭示人们,与其在小盆里养花,不如在大地上植花;与其在家里饲养飞禽走兽,不如将它们放入大千世界。这种“法自然之运”的世界观,正是当今世界所迫切需要的。
如果说在“杞人”的时代,忧天“诚为太远”的话,那么,现代人忧天已成了现实的话题;如果说古人所说的天地损坏是指自然的失常和老化的话,那么,现代的生态失调则来自人为的结果。“天塌不下来”的格言已为现代科学检测数据所推翻。上世纪末,英国《独立报》以《天正从我们头顶上塌下来》为题,报道了专家对过去40年中向大气层顶部电离子层发送并返回接收无线电反向波的实验记录的分析结果,这一结果证明,大气层顶部已降低了8.045公里。至于南极上空2000万平方公里的臭氧空洞,更是为人广知。臭氧空洞主要是人类使用氟利昂制造冷剂、灭火剂、发泡剂而造成的。臭氧减少会导致紫外线辐射,造成生命物免疫能力的下降,疾病频发,生物灭绝加快。一个氟元子可以破坏10万个臭氧分子,现在全世界年排氟利昂100多万吨。这样发展下去,“天柱折,地维绝”就不再是神话。“杞人忧天” 的故事,被人作为无端忧虑的笑柄。当今,大气层污染、臭氧空洞出现以后,人们才知道,杞人之忧原来不是庸人自扰。
现代工业文明在推动社会进步的同时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诸多灾变,不胜枚举。生态环境的破坏,达到了触目惊心的程度。空气遭破坏,酸雨出现,阴霾笼天,河流污染,森林减少,水土流失,田地沙化,沙尘暴肆虐,气候反常,生物灭绝加快等等,表明环境恶化的警报全面拉响。(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