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一带一路》国学文化翠峰山论坛文集
作者:武云清
(接上文)
一、以经史为本
作为乾嘉时期的一位“通儒”,王昶最重要的学术思想是主张经、史为一切学问之本源,以“信而好古”为上。致仕归田后,王昶主讲诂经精舍,在考核学生时,便以经史为本,“问以《十三经》、《三史》疑义,旁及小学、天部、地理、算法、词章”。再联系他此前所论:“古人不得志于时,必蕲有传于后,传后者非应科目词赋之谓。”可见,与科目词赋相比,唯有钻研经学,才能传于后世。这与其经学宗尚有密切联系。王昶曾自述日:“仆《易》宗王氏,《诗》宗毛郑氏,《周礼》宗郑贾氏,此后宋元儒先之说及已有所见者,采之附注于章末,以庶几于信而好古之谓。与当时其他考据学家一样,王昶也以“信而好古”为上,但不同的是,他并不排斥宋儒之说,而以此为“信而好古”的内容之一。作为一位金石学家,他始终坚持“抱残守缺,期于征信”的原则,坚信金石是最可靠的考证材料,“金石不朽,信有征矣”,“迨雕版既行,而辗转传伪,益不可胜计,其久而可据者,惟石本耳”,并声称“金石之学,上必与经,下考于史。放故亦为学向中之最大者”。王昶精于《易》学,“余撰《郑易学通》,常悉推其说,罔不与天象合。《系薛传》谓‘仰以观于天文’及‘天垂象,见吉凶,圣人则之’者。于是益信而有征矣。”曾协助编订《金石萃编》的门人朱文藻这样描述王昶治学的严谨:“每执卷商榷之馀,辄鬯论读书稽古、诗文格律,从源诉流,皆切要实学。”(《金石萃编跋》)不妨再举一例,“文王受命称王”是后世学者争论不休的命题。欧阳修《泰誓论》提出“西伯受命称王十年者,妄说也”的观点,王昶认为此类说法“皆以臆对而非有实据也”,“余考经传注疏及汉以前书,皆云西伯受命而称王,则称王而改元无疑也,盖其证有十四焉”间就此举出十四条例证,有根有据,“信而有征”。上述例证,皆可见王昶对于考据、实证的重视。其中,“从源诉流”既是王昶“信而好古”的经学宗尚的体现,也是他强调诗乐源流的依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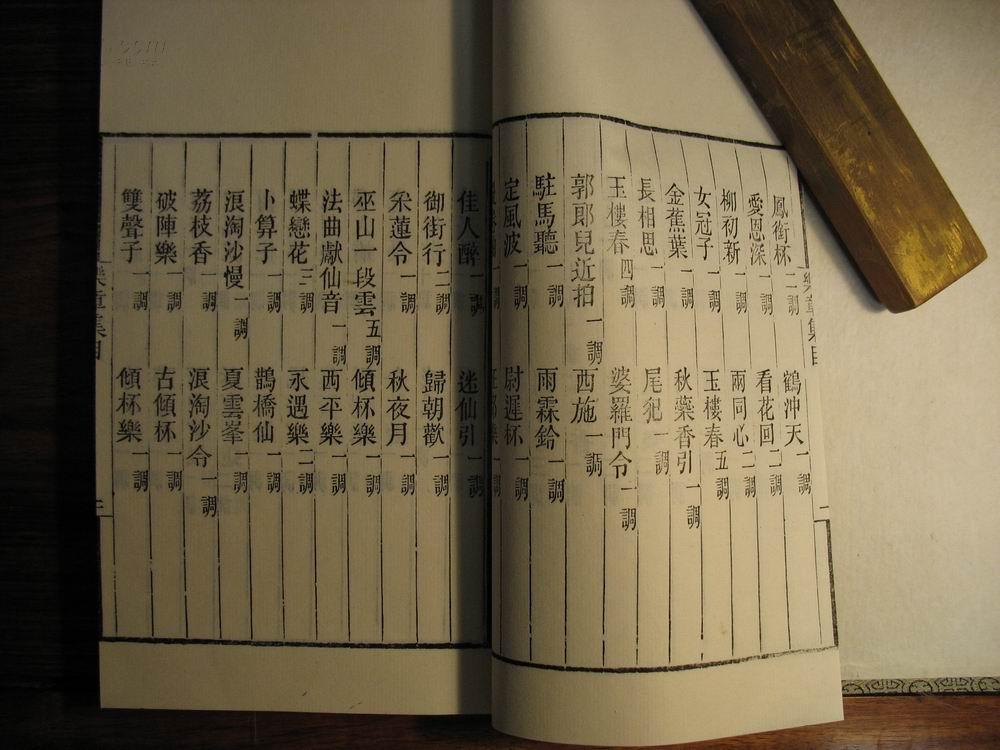
在王昶看来,“以经史为本” 的学术思想推之于诗文领域亦是如此,也就是说,“经史”是一切诗文创作的源泉和根柢。
《与彭晋函论文书》中,王昶明确提出了“湛于经史,以养其本”的文学观念:“然时文、古文不同者如此,似同而实不同又如彼。惟足下自是绝笔不为,湛于经史,以养其本,久之后达,则取于心而注于手,得其真也必矣。”强调经史的根本作用,只有以经史为本,诗文中抒发的情感才能自然、真挚。乾隆三十八年(1773),王昶称赞赵文哲《嫔雅堂集》:“大略据经史为根柢,循古人为矩矱,取丛书稗说为辅佐,又本诸萧闲真澹之志。”按他所说,赵氏诗歌之所以能成为“雅音之宗”,正在于“据经史为根柢”的特质。王昶曾为门人陈朗论学诗之法时,提出诗歌创作应该“上溯《风》、《骚》,本原经史”的主张:
前以足下所业计之,当先学七言古诗,要如洪河大江,九曲千里,奔腾汗漫中,烟云灭没,鱼龙冷啸,无所不有。经史,云烟也,龙鱼也,以气运之,以才使之,如是万为七言股市之至……当今之士捷取速化为能,规之以杜、韩已适适然惊矣,又何能上溯《风》、《骚》,本原经史?
经、史即“云烟”“龙鱼”,是七言古诗的题材所自,是诗歌创作过程中最基本的构成要素。只有具备雄厚的经史基础,才能为创作提供源源不断的养分,使诗歌蕴涵风雅之旨,极尽变化之妙。正是抱持‘‘从源诉流”的理念、王昶提出“词者,乐之条理,《诗》之苗裔”(《吴竹桥小湖田乐府序》)、“词乃《诗》之苗裔,且以补《诗》之穷”(《国朝词综自序》)、词之所以贵者,盖《诗三百篇》之遗也”(《姚苣汀词雅序》)的词学主张,通过上溯风雅推尊词体,使词体与诗并驾齐驱、同等尊贵,从而成为浙西词派全盛时期的“总结性人物”。乾隆十九年(1754),王昶所作《殿试策》中称:“惟本之身以践其实,禀之经以正其源,博之史以广其用。反覆乎唐宋诸大家之文,以辨其体,而又卓然不惑于诸子二氏之说,如是而文不工者,未之有也。”此说与朱彝尊“稽之六经,以正其源;考之史,以正其事。本之性命之理,俾不惑于百家二氏之说,以正其学,如是而文犹不工,有是理哉”如出一辙,二人都强调经史关乎诗文之好坏。朱氏明确指出:“诗篇虽小技,其源本经史。必也万卷储,始足供驱使。”而王昶“湛于经史,以养其本”、“上溯《风》《骚》,本原经史”的说法与此完全吻合,由此亦可见朱彝尊对王昶之影响。
终其一生,王昶都很重视经史对诗文的这种本源意义与基础作用。乾隆五十二年(1787),王昶在《沈柏参时文稿序》中借沈氏之言凸显“六经”之重要:“吾少时所谓思深而力锐者,大率以蠡气出之,轻心掉之,今浸淫于六经之旨,反覆于宋四子之书,始悔少时所作。”时文如能“浸淫六经”,即可达到理想境界。乾隆五十五年(1790),王昶在长沙为弟子唐业敬讲学时,也将这一思想应用到古文的写作中:‘若既本经纬史,又于诸家中择一性之所嗜者,熟复而深思之,久之,深造自得,旁推交通,自尔升堂入室。”乾隆五十七年(1792),《壬子顺天乡试录后序》又说:“窃谓文以载道,而道备于经。古之学者,读《春秋》如未尝有《诗》,读《诗》如未尝有《易》。盖三年通一艺,十五年而五经通,然后知类通达,强立而不反,谓之大成。后世士子,或殚心词赋肇悦之术,于经义忽焉不详;或杂然习之,不求其端,不讯其末,其发于文章也,于斯道奚裨焉。”指出当代士人不精经义、不考究竟之弊,从反面凸显文章中“经义”的不可或缺,体现了王昶“以经史为本”的思想。(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