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一带一路》国学文化翠峰山论坛文集
作者:王沁凌
(接上文)
问:“圣人之经旨,如何能穷得?”日:“以理义去推索可也。学者先须读《论》、《孟》。穷得《论》、《孟》,自有个要约处,以此观他经,甚省力。《论》、《孟》如丈尺权衡相似,以此去量度事物,自然见得长短轻重。某尝语学者,必先看《论语》、《孟子》。今人虽善问,未必如当时人。借使问如当时人,圣人所答,不过如此。今人看《论》、《孟》之书,亦如见孔、孟何异?”(《河南程氏遗书》卷第十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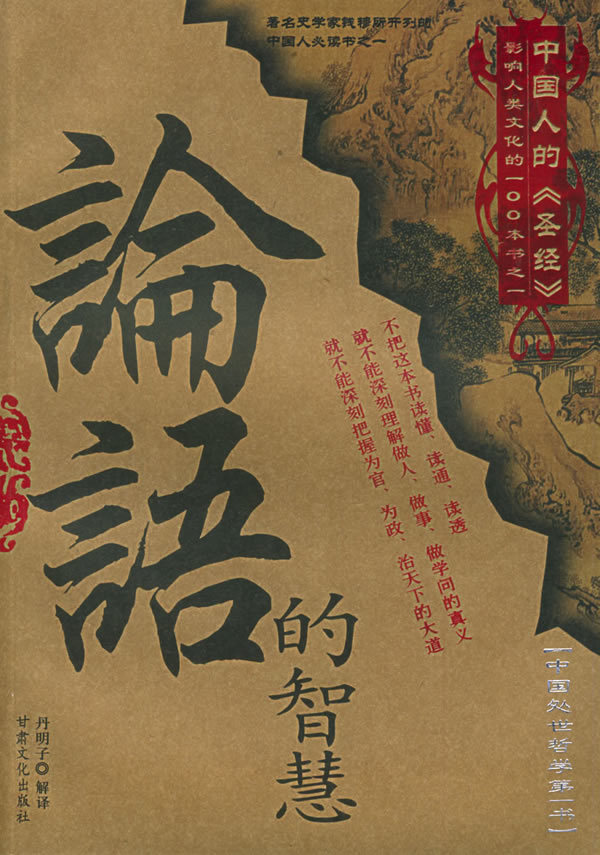
棣初见先生,问“初学如何?”日:“入德之门, 无如《大学》。今之学者,赖有此一篇书存,其他莫如《论》、《孟》。”(《河南程氏遗书》卷第二十二上)
学者以《论语》、《孟子》为本。《论语》、《孟子》既治,则六经可不治而明矣。(《河南程氏遗书》卷第二十五)
初学者面对丰富的经籍,应先求“入学之门”与“治经之本”。“入学之门”是方便接引学者进入穷经明道之学的经典,为《大学》、《论语》、《孟子》。《大学》有三纲八目,从修身至于治国,次第分明,且合于程子所说的“治体”;《论语》、《孟子》是孔、孟思想的直接呈露,学者读之有如亲炙,且二书的内容较少而不驳杂,比于他经可谓纯粹。若借宋儒说法的方式,可以说这三书高明如天而不玄远,亲切如地而不卑浅,既适于导引学者入门,也应当成为求道学者终身“悠游涵泳”以体会思索的著作。正因如此,这三书,尤其是《论》、《孟》不仅成为“入学之门”,更居于“治经之本”的关键地位。所谓“治经之本”,即经典中的经典,众经的“尺度权衡”,圣人之言的精义。掌握了《论》、《孟》中的义理,就如同掌握了圣人衡量裁定万物的标准,“自然见得” 六经之中的“长短轻重”。二程虽然也引用、讲论和注解六经,但他们既云《论语》、《孟子》既治,则六经可不治而明”, 表明他们对六经并非一视同仁。他们自己的学问,大概也多是从《论》、《孟》这二书中体贴研求而来。后来朱子所说“《论语》易晓,《孟子》有难晓处。《语》、《孟》、《中庸》、《大学》是熟饭,看其它经是打禾为饭”,于二程处已发其端。
二程呼吁并且教导学者,把经典看作与己身息息相关的对象,把读经穷理当作探索圣人之道的途径,一切与经典发生的联系是为了有用于当下,使当前的人与政治均能循着经典的呈示而向理想中的圣人与王道趋近。在二程眼中,“道学” 本身亲切鲜活而又独立不改。他们一生都以明道、传道为已任,死而后已。程颢殁后,程颐这样总结其兄的事业与成就:
周公没,圣人之道不行;孟轲死,圣人之学不传。道不行,百世无善治;学不传,千载无真儒。无善治,士犹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诸人,以传诸后;无真儒,天下贸贸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灭矣。先生生千四百年之后,得不传之学于遗经,志将以斯道觉斯民。天不愁遗,哲人早世。乡人士大夫相与议曰:道之不明也久矣。先生出,倡圣学以示人,辨异端,辟邪说,开历古之沉迷,圣人之道得先生而后明,为功大矣。(《河南程氏文集》卷第十一,《明道先生墓表》)
“道学”与“道统”是宋儒特有的发明,其后相继而出的“学统”、“政统”云云,均赖“道统”而后明。欲明“政统”与“学统”者,须先明“道统”、知“道学”;于“道学”登堂入室者,于“政统”与“学统”如视诸掌。无论“道统”、“学统”还是“政统”,称 “ 统”者皆有宗有源,其宗与源皆有传有流;然而在千百年的历史变化中,“统”之传流总是波折动荡,故其宗其源所呈现的理想再也没有出现过。在《明道先生墓表》中,程颐称其兄“生千四百年之后,得不传之学于遗经,志将以斯道觉斯民”、“开历古之沉迷, 圣人之道得先生而后明”,大概是前无古人的评价。这番话,与孙复的“取诸卓识绝见大出王、韩、《左》、《谷》、《公》、杜、何、毛、范、郑、孔之右者,重为批注,俾我六经,廓然莹然”是何其相似。以二程子为代表的北宋初期的儒者,自信能够在圣人之学“千载不传”之后, 重新阐明发扬之,这与他们“自我为法、前无古人”的学问精神是分不开的。他们对“道统”的发现、对“明道之学”的阐扬,反映着他们对孔子以后发展了千四百年的儒学传统的判分,这种判分逐渐成为他们构建当时学术的一种基本共识。 程颐为其兄所作的《行状》和《墓表》是理学发展史中的重要材料,对程颢学问的评价,及时人表其为“明道先生”的举动, 代表了道学兴起之际的学者对自身学术目标与文化使命的定位。这一定位给后来的儒学发展造成 了深远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