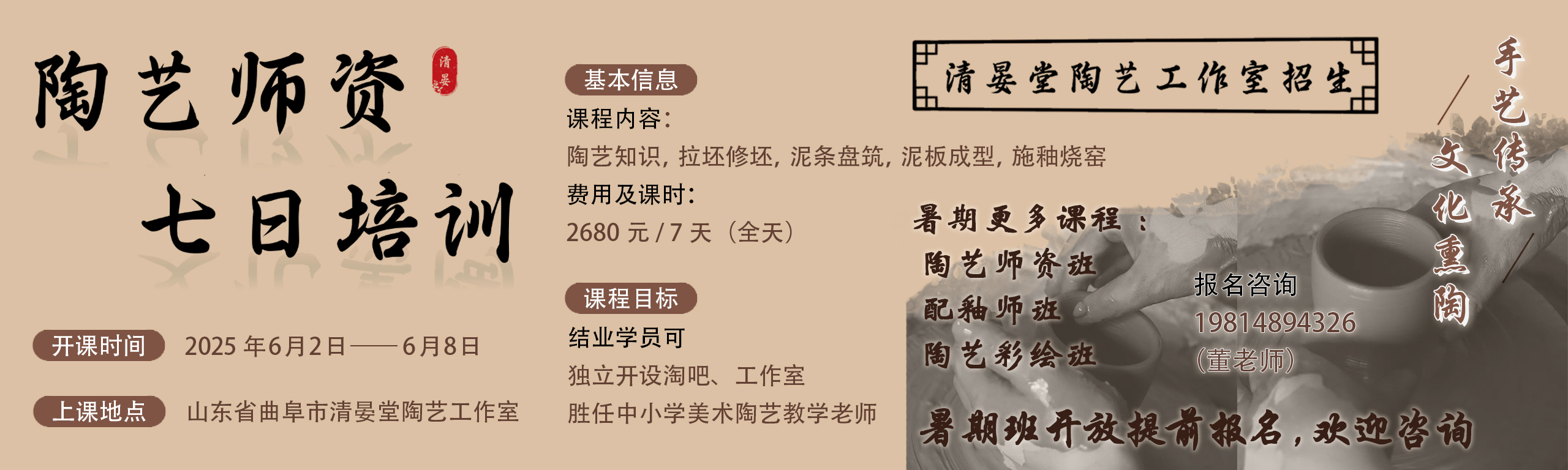来源:《一带一路》国学文化翠峰山论坛文集
作者:成兆文
(接上文)
八、儒学道统与黄帝
由于中华民族位于亚洲大陆深处,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原创文明体,这决定了,它自身的精神演进必须倾听自己的历史脉动。毫无原则地引进吸收异质文明,也许在蕞尔小国可以办到,但面对一个原创性的文明体的时候,显然就会失效。这种异质性越大,引发的应对与反弹就越强。这一点,被中国近代缓慢转型中的各种遭遇反复证明。

在孝道的角度看,未来是过去的合理延伸。未来不是时间的断裂。那么,什么可以成为人们文化上的行孝对象呢?
汉代人解决这个问题的两种办法,现在看来并不是一时兴起,而是深思熟虑后郑重的文化选择。选择儒家作为意识形态的基本框架,实际上表明了将承继儒家根本的伦理纲常。然后,在司马迁那里,历史有了开端,而且是匈奴人、汉人等有了共同的开端——黄帝。这一良苦用心实则是对儒家孝道文化的躬亲践行。黄帝不仅仅是汉人的精神之父,而且是其他人的精神之父。这就一下子构造出了一个共有的精神共同体。
儒学道统把自己的开端般放置在 三皇五帝时代,其发展线索般的表述是“祖述尧舜,宪京文武”,经过周公而被孔子集大成。唐代韩愈认为这个道统在孟子之后不传,俨然有舍我其谁的道统勇气。后世论者把尧舜为儒家道统之开端,道家汉代后黄老并称,这就似乎把黄帝划到道家道统的阵营里去了。其实,从精神共同体的角度看,黄帝不但是道家之发端处,更是儒家道统的关键性肇造者。
汉代之前,中国文化无疑有着非常成熟的形式,但是,江山统后,拿什么来函摄人们的精神,让天下真正归心?这思想任务 无疑给了司马迁、董仲舒等人,只有他们才有这种思想的敏感性,才真正“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在此之前的历史文献,只是随地散落的一件件事情记述,它们既没有内在的逻辑,也看不到共通的精神指向。在古文经学家看来,“六经皆史,然而,这些经典相互间看不出思想的契合,尤其,编年史实则是流水账, 尽管从中有着知任察来的思想张力,但史学本身的视野仍然是有限的。《春秋》 是非常重要的儒家经典,却对普国之前的事情言不发。换言之,在汉代之前,中国文化的源头问题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只是到司马迁等人那里,寻找共同的祖先成为自觉行动。
黄帝在汉代之前就以口口相传的形式流布,虽然汉初道家创制出了黄老之术,但黄帝本身的精神始源作用并未凸显。而在司马迁之后,有关黄帝的事迹就突然间增加了。在《黄帝内经》中,黄帝成了向得道者广成子求教的谦虚学生,甚而,许多后世论者言之凿凿认为该书成本于汉代。在司马迁那里,黄帝的地位大大提升,他不但拥有超凡的神力,而且是当时所有民族共同的祖先。也可以说,夸张其神力是为了这一论断 做铺垫的。
黄帝的谱系虽然复杂,但在司马迁的算术中,它传了没有多少代就进入到了尧舜禹时代。细心的读者会追问,黄帝之前究竟是什么样子?他的后代谱系为何显得线条粗犷?
这一问题在《汉书》中以另一个形象解决了。 司马迁对伏羲是只言片语,班固则对伏羲大书特书。易经的作者不仅仅是文王和孔子,而是开启文明之门的龙祖伏羲。在此之前,有关伏羲的传说都是异常简略的,甚至可以说,伏羲氏远观近譬的画卦行为也有着汉代行文的痕迹。但在汉代后,尤其是《汉书》之后,有关伏羲和女娲的故事就越来越生动具体和内容庞杂。有关伏羲的形象大多出自汉墓,尤其是蛇身人面图,从汉代或者严格说从班固之后,在各个地方都可以见到。但是,人们尚未找出一个比汉代还早的生动有趣的伏羲图。尽管蛇首人身是古代世界性文化现象。
20世纪早期,新文化运动和顾颉刚发动的疑古思潮内在都是历史虚无主义的体现,是丧失文化自信心的外在表现。大禹是一条虫, 三皇五帝都是古人的信口开河。顾颉刚的疑古主义引来中外有关人士的欢呼。但也就在那个时代,殷墟甲骨文发现了,王国维提出的双重证明法首先证明了殷商文明的存在。得源于新时代中国的大拆大建工程,许多地下沉睡几千年的文物重见天日。文物的形制和各种文化遗址都在还原一个真实而更为久远的历史文化图景。 疑古思潮本身成了被批判的对象。李学勤倡导的走出疑古时代的口号,质疑者不少,拥趸越来越多。
九、伏羲与龙:新的道统象征
伏羲的地位因其“一画开天”而开始飙升。女娲在儒家文化语境中本来受到某种抑制,但因与伏羲的亲缘关系,被人们不断提起,二者合二为的趋势明显。
陇西成纪在文献中被记载是羲里娲乡,当然,这个仍然是汉代的文化记忆。伏羲散见于先秦文献和传说,但只有到班固那里,寻找一个更加久远的精神共同体成为自觉行动,人文初祖是一种必要的追溯与重塑。随着甘肃秦安大地湾文化遗址的发掘,其与伏發女娲的有关传说,在文化内容上、形式上,关键还在时空点上的高度契合,这就把历史传说越来越接近信史。
今天,面对大地湾一抹黄士,卦台山下神奇天然的太极图,伏羲庙那种明代起就官民祭祀留下的文物规制,历史之宏图,是真是实?我们既不能幼稚地认为,伏羲就是一个 超级英雄,元个寿命特长、力气很大、 智慧很杰出,那个迥异于人的超人,单就伏羲氏的十四项功德就超出了人创造发明的可能界限。但又不能说包括司马迁在内的古人在撒谎,因为,从文化遗留的本身而言,反推过去,必然存在类似伏羲女娲这样的人,尽管他不可能是具体的单个人,更可能是一个创造的英雄群体。类似于大地湾文化遗址的发掘工作还将继续,其丰富之内容继续释放,但即使把所有的地下文物都翻出来,也不会找到非常完整的伏羲图景。虚实之间,藏着中华传统文化的大秘密。虚实相间性牵涉到中国特有的历史观,用单纯先生的话说伦理性的历史观,不同于黑格尔逻辑性历史观、现代科学性伦理观、印度神秘性历史观。东亚儒家文化圈中都有着向历史追溯寻找精神之根的伦理冲动。而这一点, 恰恰影响了后世的所谓民族性。
当人们惋惜近代中国甚至是宋代以来中国人精神缺乏必要的刚健之气的时候,我们以历史的目光看到,精气神的东西是可以塑造的,民族性是可以改变的。那个为汉代奠定精神共同体的黄帝和伏羲,都为形成大统-而富有活力的大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今天,中国自上而下都意识到,社会价值建构已经到了需要强势引导的时候。随顺人的本能要求,不但难以为继,而且,它自身缺乏必要的凝聚力。伏羲是龙的化身。龙是包容性、克坚攻难的文化象征。今天,由于传统文化在制度层面的退出以及信仰本身的坍塌,中国社会价值的扁平化已经达到了无法容忍的程度,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个精神象征。
新的价值系统必然既要契合国家发展的阶段与民族特性,又必然要契合人本身具有的先天性差异这一基本事实, 因而,正常的社会价值观必然是立体的,是各安其位的。是脚踏大地的,又是仰望星空的。我们告别英雄的时代太久了,金钱宰制下的犬儒主义即使是实然的全球化生活状态,但并不代表其应然的理想未来。今天,怀揣百年民族复兴梦的中华民族,既需要超越初始本能的物质欲望,恒久开掘经济发展动力,更需要召唤昂扬向上的中华民族的精气神,在理想与现实当中取得恰当的平衡。这两件事共同的要求是做好中华民族的铸魂工程。
对于一个编延永续的文明体来说, 回顾过去就是着眼未来,返本开新是化历史的经验为当下的智慧,继承是为了更好创新。同时,传统文化既是包容的又是创新的,我们在优秀的传统文化中汲取力量,又在为未来创造新的传统。这就要求当代学人以更加自觉的历史意识和思想重构性,有序持久释放厚重的精神资源,义为当下和未来的中国精魂塑形。
伏羲是龙的化身。龙是包容性、克坚攻难的文化象征。龙或潜于九地之下,或动于九天之上,至刚至柔,变化无穷。龙既可以从现实当中找到必要的原型,又不同于现实中任何现实当中的“百出”。龙的形象从产生到定型,从辽宁的红山龙查海石堆龙到元代龙的形象定型,龙的现象演变至少历经了七千多年的历史。这个漫长的演变已经造就了龙作为中华民族的精神象征已然成熟,而龙本身的精神含义是需要填写的,它可以有不同的含义,但它又深契中国人的心灵结构。
简单说,“伏羲(女娲)——龙”,这就是多元一体的文化结构,龙本身是大孝文化的遥远外的呼应,伏羲是未来中国文化的招魂者,也将是未来需要着力打造的中华道统的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