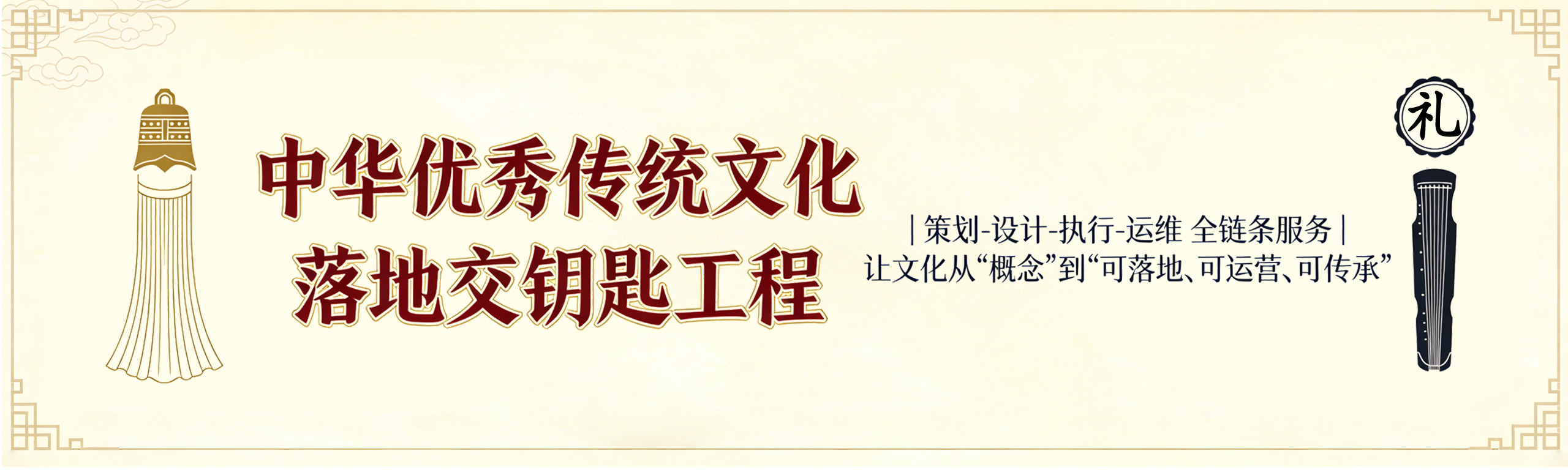作者:胡健
宋明理学与美学的关系近年来已引起一些学者的注意与研究。探讨宋明理学与美学的关系有两方面意义:一是扩展丰富理学研究本身;一是加深我们对中国美学史的理解。这篇札记拟就宋明理学与美学相关的三个方面谈点粗浅的看法。
一、”乐”道德境界的准审美超审美特征
许多学者在比较东西方哲学时指出,中国传统哲学(特别是儒家)是以重道德重伦理为其基本特征的。先秦儒家曾把仁人、君子、圣人乃至仁政当作自己哲学追求的向度。而有”新儒学”之称的宋明理学因其思辨水准的加强,更使这种追求的向度哲理化本体化了。把道德伦理本体化是宋明理学最基本的特征,也是宋明理学理论成就的标志。尽管宋明理学有关学、闽学、陆学……之别,有气本体、理本体、心本体之争,但追求道德伦理的本体化的倾向与努力却完全是一致的。
宋明理学那些精微而又博大的思辨体系的产生是有其深刻的历史与现实的原因的。张载《西铭》把这一点说得十分清楚:”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理学家们对《西铭》之所以推崇备至,原因正在于它表现了否定佛老、重振儒道,承认感性世界的真实性,肯定现实人间封建秩序的合理性与必然性的现实用心。
宋明理学的道德本体论是通过一套哲学范畴思辨地展开的。以集大成的朱熹哲学而论,他把自己哲学体系的本源与归宿都归结为”理”。”宇宙之间,一理而已”,他认为理是先于万物”无形迹无情意”永恒不变的精神本体。那么,这个”理”又怎么与现存世界发生关系呢?朱又提出”气”范畴,认为理不仅在气先,亦在气中,”无是气,则理亦无挂搭处”,”若气不结聚时,理亦无所附者”,他还用月映万川来解释抽象的理与具象的理之间的复杂关系。”天地之间,有理有气。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是以,物之生,必禀此理,然后有性;必禀此气,然后有形”,宇宙论不过是人性论的基础,落实到人性论上朱熹指出:”性即理也,在心唤作性,在事唤作理。””在人,仁、义、理、智,性也,然四者有何形状,亦只是有如此道理。有如此道理,便做得许多事出来,所以能恻隐,羞恶、辞让、是以也。譬如论药性,性寒、性热之类,药上也无讨这形状处,只是服了后,却做得冷、做得热的,便是性。”朱熹认为,人要”全其性”,必须”格物””致知””穷理”,朱熹主张”义理不明如何践履”的”知”先于”行”,并认为人”一旦豁然贯通”便可悟到伦理本性(天理)达到”极高明而道中庸”的精神境界。
然而这些与美学有何关系呢?孟子曾经指出:”理义之悦我心,犹刍豢之悦我口”(《告子章句下》),宋明理学确实把这种境界突出出来了,它既是”道德自律”(哲学)的境界,也是”精神自自”(心理)的境界,李泽厚指出它具有”属伦理又超伦理、准审美又超审美”的特征是很准确的。先秦美学中,”乐”是一个标志着审美快感的美学概念,宋明理学家也常借”乐”来描绘他们体道明道时的带有超经验意味的美感。程颢在著名的《秋日偶成》里写道:”闲来无事不从容,睡觉东窗日已红。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风云变态中。富贵不淫贪贱乐,男儿到此是豪雄。”在程颢看来,学并非是以追求外界的知识为最终目的的,而是为了寻求达到道德境界的,而这个境界也是审美境界,所以他说:”学至于乐则成矣。笃信好学,未知自得为之乐。好之者,如游他人园圃;乐之者,则己物矣。””自得”、”己物”显然指达到了自身的道德境界,真正体验到了”孔颜乐处”之”乐”。朱熹对道德境界的”乐”也有论述。他说:”私欲克尽,故乐。”因为与万物为一,无所窒碍,胸中泰然,岂有不乐!””凡天地万物之理,皆具足于吾身,则乐莫大焉。”朱熹竭力形容的这种非逻辑的非认识的靠自身体验到的与天地万物同流的道德境界(理),实质上也是审美境界(乐),它们实质上是合一的。先秦的”乐山乐水”的”乐”,在宋明理学中从一般的审美概念已经转化为具有深刻哲学意味的准审美超审美的特殊概念,并把宋明理学的准审美超审美性充分点明出来了。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从”理”开始最终又回到人对”理”的体认,并认为这种体认的境界在于”乐”-﹣宋明理学家虽分歧点很多,但对道德境界的”乐”的特点的看法却很一致,这是必须注意的。宋明理学家以道德为本体,一方面突出高扬了人的社会性、伦理性,有其深刻之处,另一方面把道德本体抽象化绝对化又带有保守性欺骗性。无论研究理学本身,还是研究理学与美学,对宋明理学道德本体的”乐”的境界都是必须重视的。
二、文与道:理学的文道论
文道说是我国古代美学中的一个重要内容。一般说来,”道”是对文章的思想内容而言的,”文”则主要对文章的词彩结构等形式因素而言的。许慎《说文》:”文,错画也。”意谓不同线条交错为美观的视觉形象,古人不仅用它来指文章的形式美,也用它指大自然的形式美。宋明理学家不少人对文道问题发表过意见,他们的文道说在中国古代美学史上特色是很鲜明的。如前所说,宋明理学追求的是”乐与天地同流”的道德境界,”文”的独特审美价值在他们的理论体系中当然不会居于十分重要的位置。虽然理学家们也写过一些好诗文(如周敦颐的《爱莲说》和朱熹的某些诗),但理学家推崇的超验的”道”(天理)必然使他们谈论文道时出现重道轻文的倾向。
不妨抄录理学家的一些原话。周敦颐说:”文所以载道也。”他把”文”比作车子,认为它本身并无价值,这样”文”便成了载”道”的工具了。程颐把这种倾向推向极端:”问作文害道否?曰:’害也’。凡为文不专于意则不工,若专意则志局于此,又安能与天地同其大也。《书》曰:’玩物伤志’,为文亦玩物也。”其实,专意于文未必就局限于词章间,也可以通过辞章来反映现实生活。而在”与天地同其大”的道学标准之下,”为文”成了”玩物丧志”,这显然是对文章相对独立的审美价值的否定。他还主张”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何也?和顺积于中,英华发于外。故言成则文,动则成章。”道德修养对写作是重要的,但仅凭伦理道德就能写出好文章,这种一味排斥为文技巧的说法是经不住实际检验的。
声明:该文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国学百科网系信息发布平台,仅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