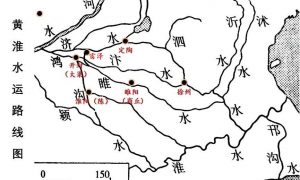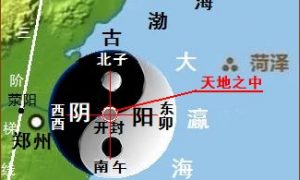作者:刘鄂培 竺士敏
但是他又区分理、气两物的顺序为本、次,主、从:“有是理便有是气,但理为本。”“气之所聚,理即在焉,然理终为主。”理既然是本,则气为次;理既然为主,则气为从。朱熹哲学,从二元论的倾向。又走向了“理一元论”。
理和气(或事)谁先谁后?这个问题十分重要。程颐对此未作明确的回答,朱熹却说得十分清楚:“未有这事,先有这理。”“未有天地之前,毕竟也只是理。……有理便有气,流行发育万物。”朱熹的“理在事先”说使他的“理一元论”在逻辑上更臻缜密,自成体系。
二、冯友兰先生的“接着讲”
冯友兰先生的哲学体系完成于1938-1946年,包括:《新理学》、《新事论》、《新世训》、《新原人》、《新原道》、《新知言》,合称为“贞元六书”。其中《新理学》是冯先生“新理学”哲学体系的总纲。
冯先生的哲学是“接着讲”,明见于《新理学》一书的《绪论》:“我们是’接着’宋明以来的理学讲的,而不是’照着’宋明理学讲的。”宋明理学有三个流派,冯先生是“接着”哪一个流派讲呢?我们从他的著作中可以找到答案。在《新理学》中冯先生批判清李塔的“理在事中”,他说:“李恕谷(塔)说,理学家(指程朱)以为’理在事先’而其自己(指李塔)以为理’即在事中’。若所谓’在存在之义,则理是无所在的。理既不能’在’事上,亦不能’在’事中。理对于实际的事,不能有’在上’’在中’等关系。”冯先生批判“理在事中”,实为赞同程朱的“理在事先”。在 1938年,冯先生在另一著作《中国哲学史》中对朱熹的“理在事先”说作了如下的解释:“若按逻辑言,则’须说先是有理’。盖理为超时空而不变者,气则为在时空而变化者。就此点言,必’须说先有是理’。”意思是说,理与气的先后,不是时间上的先后,而是逻辑顺序上的先后。这亦表明冯先生在理事关系上是赞同程朱的。
从上文冯先生对“理在事中”和“理在事先”的两种态度来看,冯先生的“接着”宋明理学讲,应是“接着”宋明理学的“程朱之学”-讲。这个问题,冯先生在1984年《三松堂自》中作出了明确的回答:“《新理学》所要’接着讲’的,也就是关于这个问题(指程朱’理在事先’)的讨论。”
冯友兰先生知识渊博,学贯中西。他对中国哲学的贡献,远非是“接着”程朱之学讲。他在继承中国传统理学的同时,又吸取了西方从柏拉图以来的本体论哲学。冯先生的“新理学”,区分两个世界(真际世界、实际世界),其中的“真际世界”应是柏拉图“理念世界”的中国化。在冯先生谢世之后,张岱年先生在《冯友兰先生“贞元六书”的历史意义》一文中对冯先生的哲学思想作了中肯的评价:“唯有冯先生的哲学体系可以说是中西各半,是比较完整的意义上的中西结合。”
以上所论,是冯友兰先生从1930年至1949年的哲学思想,我们认为,这一时期是冯先生“接着讲”的前期,亦即中国和西方古典哲学结合的时期。
从1949年至1990年冯先生辞世,这一时期是冯先生“接着讲”的后期,亦即中国的传统哲学与西方哲学辩证唯物论结合的时期。这对冯友兰先生哲学体系的奠定是十分重要的。在这一时期中,冯先生哲学思想的转变,主要表现在从“理在事先”转化为“理在事中”。冯友兰先生在哲学上的这一转变是经过三十多年的思考再思考,认识再认识而取得的。
1949年冬,冯先生参加了京郊芦沟桥的“土地改革”。他满怀热情地与年青学生一起工作,深入社会实践。返校后,他写下了自己的收获:“在土改工作划分阶级的时候,每一个与土地有关的人都给了一个阶级成份,或是地主,或是贫农,等等。有些人是地主,可是每一个地主的特殊情况都不同。有许多人是贫农,可是每一个贫农的特殊情形都不同。这样看,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具体的共相。具体的共相,就是共相与具体的结合,也就是一般与个别的结合。了解这个名词,我开始了解了我以前哲学思想的偏差。马列主义注意共相与具体的结合,一般与个别的结合;而我以前的哲学思想注重共相与具体的分离,一般与个别的分离。这个启示,对于我有很大的重要性。”冯先生所发现的他在哲学上的“偏差”,也正是西方柏拉图的哲学和程朱之学的“偏差”。以此为契机,冯先生的哲学思想开始了转化。
1959年,冯先生发表了《四十年的回顾》。他说:“有方的东西必定有方,但有方不一定有方的东西。如果在客观世界没有任何方的东西,那所谓的方又有什么意义呢?”这一分析已是十分深刻。
金岳霖先生于1984年谢世,冯先生撰文纪念,说“在金先生的体系里,具体共相保留了一个相应的地位,我的体系里没有。我当时(指清华文学院南迁至湖南南岳时期)不懂什么是具体共相,认为共相都是抽象,这是我的一个弱点。”之后,冯先生在写《中国哲学史新编》中,采用了具体共相,称之为具体共相的分析方法。
冯友兰先生终于完成了他从“理在事先”向“理在事中”的转变,这对中国后世的哲学,必然带来深远的影响。
1994年12月,在澳门召开了冯友兰哲学研讨会,讨论十分热烈。有的学者提出:冯先生在哲学上从“理在事先”转到“理在事中”,是否由于政治压力所致?我们并不否认有政治方面的影响。但是,象冯先生这样的大哲学家、思想家,他的哲学观是不会轻易改变的。从冯先生对理与事关系认识的变化过程看,有一个长期的认识再认识过程,有如瓜熟蒂落,自然而成。如果说冯先生这一转变是政治压力所致,倒不如说是冯先生一生勇于追求真理之结果,因为政治压力毕竟是外因而已。
有的学者提出了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冯先生晚年,从“理在事先”,逐渐转到了“理在事中”。这就违背了程朱之学“理在事先”原则。那末,在1949-1990年,这40年间,还能否说冯先生是“接着”程朱之学讲呢?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本文已经说过,朱熹哲学有理、气二元论的倾向,他十分强调理、气不相离,因此,在朱熹哲学中又隐藏着“理在事中”的思想。朱熹说:“疑此气是傍这理行,及此气之聚,则理在焉。盖气则能凝结造作,理却无情意,无计度,无造作。只此气凝处,理便在其中。……若理则是个净洁空阔的世界,无形迹,他却不会造作。气则能酝酿凝聚生物也。但有此气。则理便在其中。”在朱熹的哲学体系中存在着“理在事中”的思想,不过它被“理在事先”所掩盖了。我们可以这样考虑:冯先生晚年从“理在事先”到“理在事中”的转变,是发掘隐藏在朱熹哲学中的“理在事中”思想。如果这一考虑成立的话,则冯先生晚年哲学思想的这一转变,是对朱熹哲学的“发微”和“扬弃”。从这一意义上说,冯先生晚年从“理在事先”到“理在事中”的转变,仍然是“接着”程朱之学讲,而且是从更深的层次上“接着讲”。
声明:该文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国学百科网系信息发布平台,仅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