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孔子文化》第20期
作者:马聚英
(接上文)
二、儒家思想——中国文化内在自身发展的产物
(一)多学科研究方法综合运用,强调文明发展的连续性
如何用思想史的方法来研究一种思想的起源?“首要是关注此种思想体系的诸元素在历史上什么时候开始提出,如何获得发展,这些元素如何经由文化的历史演进而演化,以及此种思想的气质与取向与文化传统的关联”(陈来:《古代宗教与伦理》)。思想史起源研究的基点,正是思想的传承过程。陈先生将这一方法运用在研究儒家思想的根源上,通过分析三代的文化发展历程,找寻儒家思想和文化气质的最早存在,提供了一个注重宗教–伦理体系的思想文化解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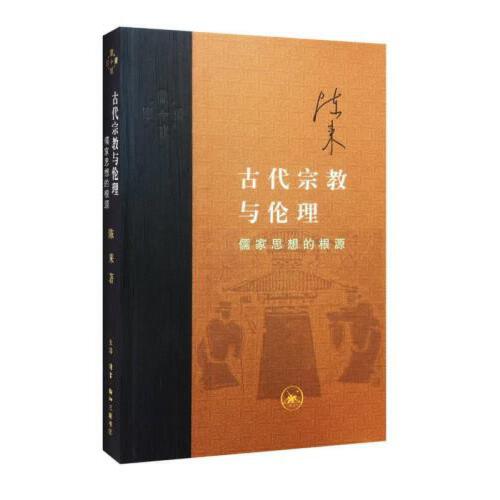
本书在内容上层层推进,第一章到第七章从巫现、卜筮到祭祀,再到天命、礼乐、德行,陈先生从宗教人类学入手,交叉使用人类学、宗教学、文化学、历史学、考古学等方法,详细地叙述了三代文化的发展历程,这也是在研究方法上的创新。运用宗教人类学的方法和概念,以宗教–伦理观念的演变为中心,陈先生将三代文化的演进历程归纳为从巫觋文化、祭祀文化进而发展为礼乐文化,而与之相对应的宗教则是从原始宗教到自然宗教,又发展为伦理宗教。那么这三种文化之间是一种什么关系呢?或者三代文化与儒家思想又有什么关系呢?
不同于雅思贝斯的“轴心时代”理论,陈先生指出,“中国古代文明演进的一大特色是文明发展的连续性。固然,春秋战国时代的精神跃动比起以前的文化演进是一大飞跃,但这一时期的思想与西周思想之间,与夏商周三代之间,正如孔子早就揭示的,存在着因袭损益的关联。因此中国哲学的第一次繁荣虽然是在所谓轴心时代,但必须看到,儒家为代表的诸子百家并没有一个神话时代作为背景和出发点,宗教的伦理化在西周初即已完成”(陈来:《古代宗教与伦理》。“所以,从注重文化的连续来看,公元前500 年左右时期内的中国文化与三代以来的文化发展的关系,乃是连续中的突破,突破中有连续。”(陈来:《古代宗教与伦理》,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5页)。所以,三代文化之间及儒家思想与三代文化之间的发展是有继承性的,即“包容的连续”。在此,人类学上“文化模式”和“精神气质”两个概念的运用尤为重要。陈先生指出“西周文化所造就的中国文化的精神气质是后来儒家思想得以产生的源泉和基体”(陈来:《古代宗教与伦理》)。这是儒家思想与西周文化之间的关系。而西周的思想又以夏商文化的历史发展过程为背景和基础,“西周文化又是三代文化漫长演进的产物,即从巫现文化、祭祀文化而发展为礼乐文化,从原始宗教到自然宗教,又发展为伦理宗教,这样才形成了孔子和早期儒家思想产生的深厚根基”(陈来:《古代宗教与伦理》)。文化之间的这种连续性,说明了儒家思想的产生必定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是三代文化发展的产物。因此,陈先生说“儒家思想是中国文明时代初期以来文化自身发展的产物。”
(二)先导之功–引导古代思想史的研究回到“前轴心时代”
“儒家思想是中国文明时代初期以来文化自身发展的产物”,陈先生将古代思想史传承的起点追溯到殷周之际,这无疑大大延伸了思想史研究的领域。“陈先生的研究是在一个新的宏观的学术背景下,凸现出中国文化’轴心时代’与’前轴心时代’之间存在的连续性这种特殊品格。因而,在一种新的思想史研究的意义上,陈先生的研究引导着古代思想史的研究回到,前轴心时代””(王楷:《“以哲学家的写法作古史的研究”–陈先生儒学及诸子学思想史前更研究述略》,邯郸学院学报,第15卷第2期)。陈先生自己在回答《古代宗教与伦理》这本书的意义时提到:“现在看来,这本书对其他学者或多或少发生了一些影响。近年来不少学者开始注重巫史文化问题,注重轴心时代文化与巫史的关系,应该说都与本书有些关系,至少可以说,本书在研究中国上古思想时所提出的问题和结论,对晚近的讨论有先导之功”(方旭东:《好学深思,心知其意–陈来教授访谈》,《学术月刊)2002 年第1期)。的确,在此之后,很多致力于古代思想史研究的学者对“巫史”问题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李泽厚先生便是其中的一位。
李泽厚先生在《说巫史传统》中提到,中国思想史的最大秘密:“巫”的基本特质通由“巫君合一”、“政教合一”途径,直接理性化而成为中国思想大传统的根本特色。本句话可以概括为:“巫”特质–理性化–大传统根本特色。换言之,李泽厚先生的中心观点为:中国文化–哲学特征来自原始巫术活动的理性化。那中国文化的特征是如何经由巫术礼仪的理性化而最终形成的呢?在 2005 年的《“说巫史传统”补)中,李泽厚先生作了进一步补充,指出这个理性化的核心是由“巫”到“礼”,而“祭”的体制的确立是这二者转换和衔接的核心。简言之,李泽厚先生所说的这个理性化的道路可概括为“巫–祭–礼”。
(三)儒家文化的产生——漫长的文化理性化过程
陈先生认为儒家文化的产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文化理性化的过程。其所论述的这个理性化过程正可以与李泽厚先生作一比较。
不同之处有两点。首先,两人的叙述角度不同。陈先生是从宗教–伦理发展的角度,亦可以说是宗教理性化角度来总结这条理性化道路的,与韦伯所说的“世界祛除巫魅”是一致的。书中展示了中国文化发展的道路,从巫觋文化、祭祀文化而发展为礼乐文化,与之对应的宗教是从原始宗教到自然宗教,又发展为伦理宗教。陈先生借助弗雷泽对巫术和宗教的区别来区分巫觋文化和祭祀文化,指出巫术文化是“借符咒魔法的力量来使自然界附和人的愿望”,即强迫、压制自然和神灵,这是原始宗教的阶段,或可以理解为尚未进入到宗教阶段。而殷商时主导的宗教信仰–行为形态,是“努力通过祈祷、献祭等温和谄媚手段以求哄诱安抚顽固暴躁、变幻莫测的神灵”的祭祀文化,其对鬼神的信仰与行为,变现出殷商文化的意识已经完全超出巫术阶段,处于自然宗教的多神信仰阶段。到了周,陈指出宗教又发生变革,即从自然宗教过渡到伦理宗教。殷人信奉的上帝与人世的伦理无关,而到了周,周人把历史现象上升到宗教和哲学的高度,将天命与历史人事关联起来,将人世的伦理道德赋予天,如此中国文化便由自然宗教发展为具有伦理宗教水平的文化形态,价值理性在文化中开始确立根基。
而李泽厚先生以巫的“特质”为核心,经巫到祭再到礼,是从“巫术礼仪”的理性化来阐述的。第一阶段:巫–祭。从巫到祭,先要看史的作用。李泽厚先生将“史”视作继“巫”之后进行卜筮祭祀活动以服务于王的总职称。从巫到史,经过“历史经验”“天象历数”和“军事活动”等因素,巫术活动中的非理性成分日益减少,而理性、现实的成分日益增多,神秘的情感、认识逐渐有了理性的依据。之后通过祭礼活动,原始巫术活动中复杂繁多的规矩已演变成了人们要遵行的礼仪制度了。
其次,对待巫术的态度不同。陈先生认为巫术文化代表的是非理性,其中充斥的是神秘、不确定的力量。由巫觋到祭祀,再到礼乐,正是将巫术中的神秘、不确定因素逐渐剔除的过程。而李泽厚先生对“巫史传统”是持肯定的态度,将之作为中国文化的源头。但这样是否有些不妥呢?如宋伟在《从“巫史传统”到“儒道互补”:中国美学的深层积淀》中说:李泽厚描述“巫史传统”的重心始终在其“理性化”的过程,因而并未过多地关注其理性化的不完全性或粘连性,以及由此带给中国文化的负面消极影响,给人的印象往往是正面肯定的描述较多,而对其负面消极影响的论述一直不够明确和突出,这不能不说是“巫史传统说”所存在的缺欠与不足。需要后学进一步关注,深学覃思,还原本来,求其中正。
相同之处亦有两点。一是早期文化发展的理性化道路,两人都认为是巫–祭–礼这条道路;另外,在儒家起源上,两人都强调文化之间的继承性,即陈先生所说的包容的连续性。陈先生认为把儒家的起源直接归于巫觋文化,不仅不能认识儒家理性主义与巫术神秘主义的区别以及二者之间存在的紧张的关系,而且根本无从说明文化史和宗教史的历史演化”(陈来:《古代宗教与伦理》,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13页)。陈先生从文化史和宗教史的历史演进来看,主张区分儒家神秘主义和理性主义的不同,由此认为儒家的起源不能直接归于巫觋文化,而是中国文化内在发展的产物。李泽厚先生则认为巫术礼仪不仅是儒道两家,而且还是整个中国文化的源头(李泽厚:《说巫史传统》,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版,第43页)。以及上文引到的:“巫”的基本特质通由“巫君合一”“政教合一”途径,直接理性化而成为中国思想大传统的根本特色。李泽厚先生是从各文化的传承与保留来说,即各种文化之间相同的特质和基本精神,从这一层面来说,强调儒、道文化中的特征正是由巫文化中的根本特质和主要精神理性化而成。(未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