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孔子文化》第14期
作者:宿莽
(续上文)
先秦儒家从仁者爱人、仁者人也亲亲为大的角度论孝,关注孝子之身体,视孝为一种立人之法,成人之道,都强调了其孝论终极目的在于培养仁人志士,孝学是为已之学。如何行孝,也是紧紧围饶成人之道而论,特别是如何通过立人达人实现立已达已。这从另一方面体现了考的实用理性,在某种程度上是渗透了如何使一种行为给自身或他人带来的经济利益最大化的思想,具有一定的功利性。从这里。我们也可以更容易地理解孔门后学、儒家者言“为孝,此非孝也;为弟,此非弟也。不可为也,而不可不为也;为之,此非也;弗为,此非也”的深层含义。即孝非为孝而孝,亦非纯为孝亲而孝,孝或孝子本身更多的是在完成一个子女角色的同时去证实和成就自我。儒家“对待主义”理性告诉我们:存在者之本质并不是由纯粹自身来决定,而是在与其他存在者相对应的关系中生成的,是“自身和他者共同赋子的”。([韩]李英灿《儒家社会学何以可能》,《孔子研究》2003第1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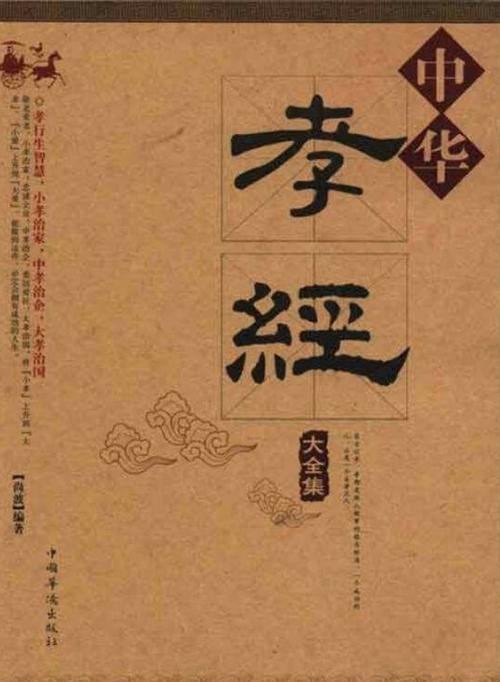
依西方诠释学的观点来看,传统经常是自由和历史本身的一个要素。甚至最真实最坚固的传统也并不因为以前存在的东西的情性就自然而然地实现自身,而是需要肯定、掌握和培养。传统按其本质就是保存(Bewahrung),尽管在历史的一切变迁中它一直是积极活动的。但是,保存是一种理性活动,当然也是这样一种难以觉察的不显眼的理性活动。”([德]加达默尔著,洪汉鼎译《真理与方法》)如果此论大致可以成立,那么上述儒家承礼论孝,事亲以礼,视孝为礼义之文理,对孝本祭礼传统的“肯定、掌握和培养”、用心保存,即体现出一定的理性色彩的“理性活动”,尽管它是有些“难以觉察”的“历史”要素;而引仁入礼、纳仁论孝,则体现出早期儒家对传统孝礼的新释和拓展,相对于传统的“孝礼之始”,孔子儒家的孝“为仁之本与”、“仁者人也,亲亲为大”则是这一传统中的“自由”要素,具有一定创新性的转化之举。先秦儒家对上古孝伦理承礼、纳仁的理性化诠释,使孝传统伦理中“历史”与“自由”两种要素相辅相成,并行不悖,都是一种哲人覃思、理性深虑的结果,凝结着一种以“情感退居次位,理性上升到主位”为首要特点的“文明思维”(冯天瑜《中华元典精神》),是早期中华文明演进中思想巨子们的集体智慧。此亦为早期儒家孝论的精粹优点所在,不可不留意。
三、孝伦理的现代转化
当下,和其他传统思想文化资源一样,孝伦理面临着被解构、重构和实现向现代的转化过程。从上述可见,承礼纳仁论孝的理性化诠释是先秦儒家孝道的精粹,恰恰也是传统孝伦理现代转化的重要思想资源,需要现代人给予足够的重视。在某些西方学者看来,传统的存活机会取决于“这些社会中理性化驱动力的存在状况”([美]希尔斯著,傅铿、吕乐译《论传统》),但这种“理性化驱动力的存在状况”不仅要求我们着眼和发扬先秦儒家孝道的精粹,还应清醒地认识到其内含的潜在弊端,如泛孝主义和偏孝偏忠。只有对二者保持足够的清醒认识,才能扬长避短。实现儒家孝伦理的现代转化,更好地发扬其有益人心世道之效用。
就精粹而论,先秦儒家提倡尊重孝礼,将亲子关系与天地同等,列为三本,存旧礼但不囿于其毂,而是又纳仁论孝,要求以亲亲为大的仁爱之心尽力行孝,以求立人达人而终可立已达己。在行孝上。他们更是提倡要一生事之以礼、敬爱父母,但不可失去理智,而是礼力相副,从义不从父,父子亦可相诤相规劝,体现出理性思维(详见另文)。其实,从更广阔的意义上来说,先秦偶家论孝背后所依托的礼、仁思想资源和伦理精神,如礼尚往来和为贵、自卑尊人、发乎情止乎礼、“礼者理之不可易者“和仁者爱人、忠恕之道、自厚薄责、先难后获得等,更是儒家文化的精粹之渊薮。历万世而不变,需要我们格外珍视和创造性化用。就此而观,孔仁孟义、礼乐文明实当为中国人走上现代的“资源与助力”(罪齐勇《中国哲学智慧的探索》)。
当然,在先秦儒家对孝的理性化诠释和构建中,出现了过度诠释、无限扩大孝作用的不理性现象,导致泛孝主义。如孟子认为“亲亲,仁也;敬长,义也。无他,达之天下也”,《孝经》日“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大戴礼记•曾子大孝)更是将孝视作“天下之大经”、“置之而塞于天地,衡之而衡于四海,施诸后世,而无朝夕,推而放诸东海而准,推而放诸西海而准,推而放诸南海而准,推而放诸北海而准”。在此基础上,孝被进一步扩大成约束各种行为的总准则,所谓“居处不庄,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莅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战陈无勇,非孝也”,以致“断一树,杀一兽,不以其时,非孝也”。这种甚至“把孝道扩张到动植物世界”的说法(韦政通《儒家与现代中国》),认为孝无处不在、无所不能,显然已经远离孝为善事父母、能事父母的本意,易陷入神化之淖,流于虚妄。汉代之后,史载有人诵读《孝经)、《周易》可以辟邪、去兵、祛灾,荒诞之至,虽有其他现实原因,但亦与先秦儒家经典里的泛孝主义体戚相关。究其文化原因。儒家既想让孝道的作用分流到家庭伦理规范上,但又有内圣之余外王的追求有关,而孝本来就曾是祭祀政教之道器,这种双重企图又继续膨胀,将孝幻化成弥纶天地的百行之大纲大本,显然失之无当,积久多弊,可以想见。
另外,在处理孝、忠两难全时,先秦儒家也有偏失致弊之处。如学者所言,儒家孝道存在“两个弊病”:一是由于孝行,侧重家庭伦理,造成国家伦理的薄弱化;一是移孝作忠,造成专制时代的愚忠主义,为专制君王所利用。(成中英《文化、伦理与管理——中国现代化的哲学思考》)这种国家伦理的弱化或被利用的两难,在历史上颇多争议,而先秦时期已埋下其根。如当时孔子与楚人叶公、孟子与桃应讨论这类问题时,孔、孟等儒家更倾向于孝亲大于忠君,提倡“父为子隐,子为父隐”、“为父绝君,不为君绝父”、“视弃天下犹弃敝蹝也,窃负而逃,遵海滨而处,终身欣然,乐而忘天下”,不免遗人之讥,引起后人争论(当代学界曾对儒家的亲亲直隐等伦理问题展开过激烈的讨论,参见郭齐勇《儒家伦理争鸣集——以“亲亲互隐”为中心),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邓晓芒《儒家伦理新批判》,重庆大学出版社,2010年;郭齐勇《儒家伦理新批判之批判》,武汉大学出版社,2011年;等书)。而到荀子及韩非子那里,倡导优先忠君以克私孝之弊,继而被后儒发挥,则走向另一极端,出现“杀身以成其忠”,“为人臣者,杀其身有益于君则为之”。此孝此忠,皆易流于愚孝或愚忠,而为后人特别是近代激烈的反传统主义者所批判,目为“奴隶之道德”(任建树《陈独秀著作法》第一卷)、“吾人精神生活之桎梏也”(易白沙《德王春秋》)。
孔子云:“观过,斯知仁矣。”诚如是,以上对先秦儒家孝伦理之“过”作的两点说明,亦大有必要。其说意在呼吁今日倡行儒家文化裨益当世者,应对传统孝道和儒家文化的优缺精糟、方方面面皆保持一定的关注和清醒的认识。对传统之精华保留一份同情、温情与敬意,对其缺失弊端之处亦当保持一份注意。如此方可为新时代下的华夏新民,最大程度上发挥“社会中理性化驱动力”的作用,以一份理性基础上的温情、热情去实现传统儒家孝道伦理的现代化,以裨益于当今国人身心两谐、社会安定、道洽政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