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一带一路》国学文化翠峰山论坛文集
作者:武云清
(接上文)
二、专于一家
“专”、“精”是与“博”相对的一种治学方法。总体而言,王昶在治学方法上,视“博而精”为最理想的治学方法:“盖古之学者,读《易》如无《诗》,读《书》如无《春秋》,又于一经中颛守一说,历数世而不变,是以立志也定,而为说也博且精。”“博而精”也就是传统儒家之“博观约取”,“博”是治学的门径,“约”则是最终归宿。章学诚强调博、约非二事,二者互相制约:“学贵博而能约,未有不博而能约者也。以言陋儒荒俚,学一先生之言以自封域,不得谓专家也。然亦未有不约而能博者也。以言俗儒记诵,漫漶至于无极,妄求遍物,而不知尧舜之知所不能也。”王昶则认为,“精”、“博”在治学过程中具有不同的意义,二者兼具才是完整的为学之道。嘉庆元年(1795)论研经之过程:“昔人三年通一艺,专守师传精古义。次乃涉猎采群言,阅年十五良非易。迩来饾订夸搜罗,摭拾星宿遗羲娥。盈科渐进圣所训,记丑而博将如何。”以唯有“博且精”,才能实现“立言不朽”,《跋稽古编》曰:“覃思深造,博而能精,殆未有不传,传久之,未有不益著且大者。”金石学中,王昶也强调征引之博,辨析之精。乾隆五十四年(1789)修葺友教书院时,王昶于所定规条中提出“盖博学者,圣学之所从入也”的论断,同时又主张“即质有不逮, 或专习经,以一说而通众说,或专习一史,以一史而通诸史,或通天文、算术,或为古文、骈体,或习诗词,或研《说文》、小学、金石、文字,各成专门名家之业”,即资历尚浅者,退而求其次,可以一经一史为师法对象,进而通经通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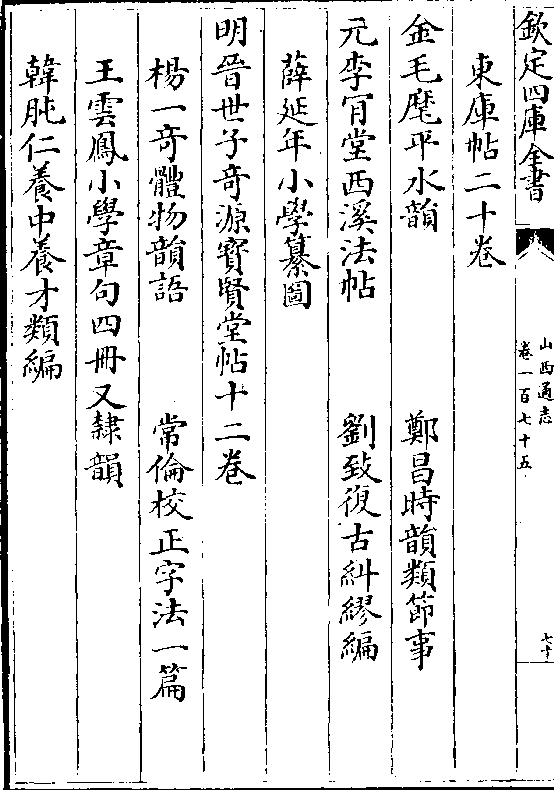
因此,王昶更倾向于“专”。《与汪容甫书》着力申说“专精”之旨:“盖以兼通必不能精,不精则必不能致于用也……今之学者,当督以先熟一经,再读注疏而熟之,然后读他经,且读他经注成,并读先秦两汉诸子,并十七史,以佐一经之义。务使首尾贯串,无字一义之不明不贯。熟一经,再习他经,亦如之,庶几圣贤循循慥慥之至意。若于每经中具数条,每注疏中数举十条。抵掌掉舌,以侈渊浩,以资谈柄,是欺人之学,古人必不取矣。”强调“精”在经学中之重要性,而且是“致用”的决定因素。“精”表现为“熟一经”,即精通一部经书,这是经学最基本的治学方法。在王昶的治学图谱中,“精”与“专”、“约”是紧密相关的概念。《困学编题词》云:“凡学要于博观约取,不约则不专,不专则不精,专乃能熟,熟乃能养。”取诸也约,守之也专。”我们发现,王昶在乾隆四十三年(1778)就已经提出“为学必专于一家”的观点:
为学之途,犹建章宫阙,千门万户,求所以入之而已矣,入之必专于一家。颇怪今世文士辄日我能经、我能史、我能诗与古文,叩其所业,率皆浮光掠影,未有深造而自得者。夫学者必不能尽通诸经也,尽通诸经乃适以明一经之旨。而一经之中分茅设蕝,若汉人之《易》,瓯异子家元矣。汉人中若家孟、若荀虞又各不同,不守一师之说,深探力穷之,于彼于此掠取一二说焉,必至泛滥而无实,穷大而失居。推之他经皆然,推之史与诗与古文,亦无不不然,故愿足下专于一家,求所以入之也。
“通诸经”是可望而不可即的理想程度,而“尽通诸经乃适以明一经之旨”。《示戴生教元》也称: “然必通诸经,乃于一经之旨,无不明晰。”钱大昕在写给王昶的书信中,也提出“通全经而后通一经”:“大约经学要在以经证经,其训诂则参之《说文》、《方言》、《释名》,而宋、元以后无稽之言,置之不道;反复推校,求其会通,故曰必通全经而后可通一经。”如此看来,在“通全经”与“通一经”的关系问题上,王昶与钱大昕的侧重点不同,前者重“通一经”,后者强调“通全经”。王昶认识到“学者必不能尽通诸经”,即《与汪容甫书》“兼通必不能精”的客观现实,转而主张“通一经”、“专于一家”的治经方法。综观乾嘉时期,“专于一家”已然成为一种学术潮流,被士人奉为圭臬。戴震强调“贵精”:“学贵精不贵博,吾之学不务博。”国朱筠主张‘‘治经当守一家之学”(汪中《朱先生学政记》)。阮元肯定考据之“精”:“为浩博之考据易,为精核之考据难。”(阮元《晚学集序》)王鸣盛不满为学之“博”:“为学之病,惟在好博。博而寡要,弊乃丛生。”(王鸣盛《蛾术编》卷八十一)当时学者不仅在学术主张上宗尚“专精”,而且身体力行,治经时也如惠栋治易学、胡培晕专于礼学、刘宝南精于《论语》等。王昶倡导“专于一家”,与学术界之主流完全合辙。
如前所述,王昶认为“专于一家”的方法不仅适用于经学,推之史学、诗学、古文等领域亦然,并屡次阐述这观点。《示朱生林一》亦云:
学诗先博学,博而约取。举古人诗,反复循玩,融洽于心胸间,下笔自然吻合。又宜先学一家,不宜杂然并学。河西女子听康昆仑弹琵琶,谓本领何杂者,正坐此病,仿一家到极至处,自能通诸家。《楞严》云:“解结中心,六用不行。”皆是诗家妙谛,仆于此事三折肱矣,可得正法眼藏,故不惜为吾贤饶舌也。
通一家,自然可以通各家,这是学诗之取径。王相劝导弟子戴教元日:“诗学,如《古诗纪》、《乐府解题》、《全唐诗》、《宋诗钞》、《宋诗存》、《元诗选三集》、《明诗综》诸书,亦宜浏览,其取法也,杜韩苏陆称最,亦以一为宗。”(《示戴生教元》)与古文以韩、柳、欧、苏四家为最相似,诗则以杜、韩、苏,陆为最。因此阮元称其诗“后宗杜、韩、苏。陆”。其实,在王昶的思想中,不论诗还是文,都须“以一家为宗”:“古文之学,世所传韩、柳、欧、苏、曾、王八家之外,《两晋文纪》、《唐文粹》、《宋文鉴》、《南宋文选》、《元文类》、《中州文表》、《明文授读》, 皆宜浏览, 博观约取,以一家为宗。”(《示戴生敦元》)
王昶认为,“专于一家”,也就是“不宜杂然并学”,最终是为了达到“熟”的理想境界。滇边戴罪从军时期,他阐述了”熟”的诗学境界:
昌黎《赠崔斯立》云:“往往蛟龙杂蚁蚓。” 盖讥其杂也。勿杂则纯,纯在熟,熟非久且渐不能。择杜陵诗,得其尤粹美者,强记而循诵之,务底于熟,使章句音节一一悬著心目,又寻绎其命意之所在,且加涵养焉。如是而驳杂之病乃除。诗词虽小道,不可以一蹴几也。矧杜陵又诗之最精深者,世人务小慧,辄欲弋获之,无怪仅得其龛犏钝涩,哆然自号为杜,而去之乃益以远。仆不喜人易言诗,尤不喜世人易言杜,正坐此病尔。《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则居之安;居之安,则资之深;资之深,则取之左右逢其源。”此非为学诗者言,然学诗而蕲底于精与深者,无以易此。惟足下勉之。
“勿杂则纯,纯在熟,熟非久且渐不能”,是上述材料的核心观点。诗词创作并不会轻而易举就能达到“工”,最关键的是要做到“熟”。而“熟”的实现需要两方面的工作:一、除驳杂之病而归于纯。二、需要经过长时间与循序渐进的过程。换句话说,王昶强调不断地学习、不断地积累,去除驳杂,归于纯然,才能达到精、深的诗境,即《孟子》所谓“深造自得”。古今诗人,能达到这种诗境的唯有杜甫。“纯” 与“专”相近,而与“杂”相对,是王昶“专于一家”的学术方法在诗学领域的极好体现。
古文理论中,王昶也主张“熟而后工”。他肯定柳宗元《报袁君陈秀才避师名书》中“慎勿怪、勿杂、勿务速显”的论文之言,提出“作文,词不患不富,要归于峻洁”凹的观点。根据王昶自己所言,他曾选取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轼四家之文,而成《四家文类》,自序云:“孔子日:‘多见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孟子日:‘博学而详说之,将以反说约也。’择则约,约则熟,熟则沈冥融冶,忽与心通,忽与手会,汨汨乎左右逢其源焉,臂之水触地而出,不审其孰为涵,孰为渑也。如是合四家为家,亦不自知肖于某家,斯为文之极工尔矣。”编选《四家文类》以纠正后世局守茅坤“唐宋八家”说之弊。主张以此四家文为最,合四家为一家”。专而熟,熟而“忽与心通,忽与手会”,左右逢源,这与《与彭晋函论文书》中“取于心而注于手”的观点一致,都需要港深于经史之学。
总而言之,王昶经学思想对文学思想的影响,在清代中期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以经史为本”、“专于一家”被他很自然运用到诗文创作与理论当中,由此可见清代中期经学对文坛的渗透,显然已经成为一种颇具普遍性的现象,很多文人都强调诗学渊源于经学,如扬州学派中阮元、汪中、凌廷堪等人也主张“为文须根柢经史”。值得注意的是,王昶虽然提倡“以经史为本”、“专于一家”,但又不受共所限,反而展现出一种比其他考据学家更为通融姿态。即使是与汉学家立异的宋学家姚肃,也借王昶之文而提出“义理、考证、词章合一”的古文创作理论,《述庵文钞序》云:“学间之事有三端焉,日义理也,考证也,文章也。是三者,苟善用之则皆足以相济,苟不善用或至于相害。今夫博学强识则善言德行者,固文之贵也。寡风而浅识者,固文陋也。然世有言义理之过者,其辞芜杂俚近如语录而不文;为考证之过者,至繁碎缴绕而语不可了当。以为文之至美,而反以为病者,何哉?其故由于自喜之太过,而智昧于所当择也。夫天之生才,虽美不能无偏,故以能兼长者为贵。而兼之中又有害焉。岂非能尽其天之所与之量而不以才自蔽者之难得与?青浦王兰泉先生,其才天与之三者皆具之才也。先生为文有唐宋大家之高韵逸气,而议论、考核甚辨而不烦,极博而不芜,精到而意不至于竭尽。此善用其天而以能兼之才,而不以自喜之过而害其美者矣。”可见,王昶并不像其他考据学家那祥过分强调“学费专精”、过分尊崇考据而贬抑词章,而能兼收“义理、考证、文章”三者之长,所作古文遂有“唐宋大家之高韵逸气”。









